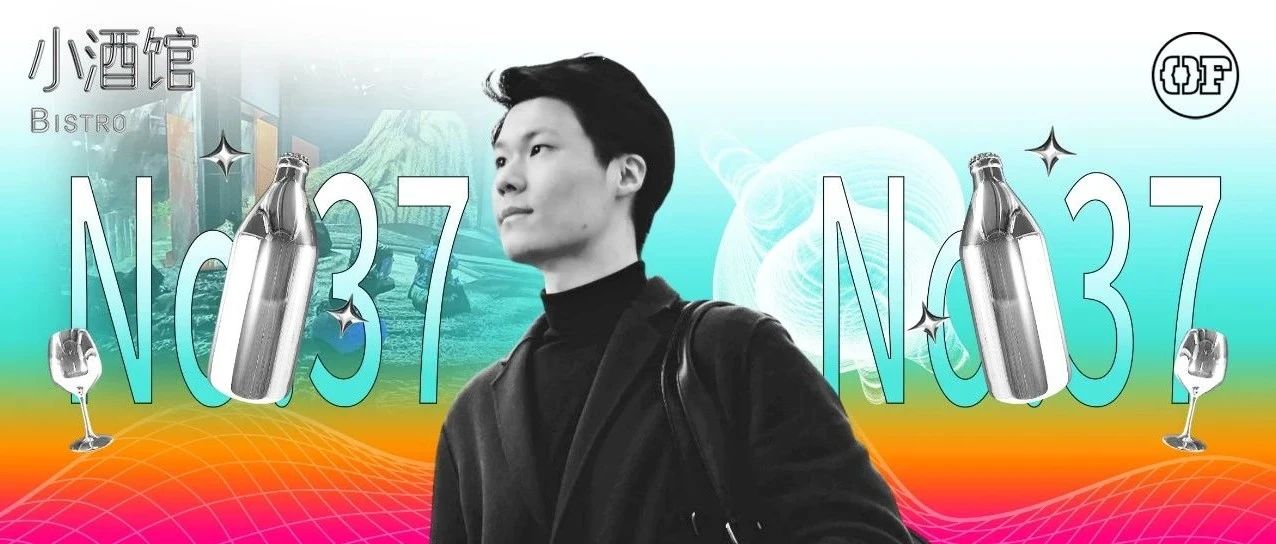马仕骅 | Shihua Ma
马仕骅,新媒体艺术家,中国音乐学院作曲系电子音乐作曲专业教师,中央音乐学院电子音乐作曲专业博士。专注于计算机音乐与视听艺术,作为跨媒体艺术家,在国际重要计算机音乐活动中持续发表相关作品。
所创作的互动多媒体类作品曾在北京国际电子音乐节作曲比赛、全国声音与音乐技术会议(CSMT)作曲比赛、全国高校数字艺术大赛(NCDA)、等赛事中多次获得奖项。所创作的新媒体音乐作品曾多次在中国、美国、欧洲等多个地区的艺术活动中上演,其中包括北京国际电子音乐节、上海电子音乐周、波兰Audio ART FEStival、2016世界电子音乐联合年会(CIME)、2018 国际现代音乐协会新音乐日(ISCM)、2020国际计算机音乐协会年会( ICMC)、2021新音乐表现界面会议(NIME)等。所作的装置类艺术作品曾于2015 B3+Beijing动态之再影像展(中央美术学院美术馆)、2018中国音乐新媒体联盟装置展、2021长沙無用美术馆“隐形的声音》装置展等活动中展出。2022年10月于上海举办作品个展《再声:RE-SOUND》。
所著学术论文曾连续两次获北京国际电子音乐节论文评奖比赛最高奖。作为交互设计编程环境 Max官方认证讲师,著有《Max/MSP/Jitter交互声音与影像创作教程》(人民音乐出版社出版,2022),该教材是由Max出品公司Cycling’74官方认证的第一部中文教程。
您好!欢迎来到OF小酒馆,先来和我们观众打个招呼吧!
大家好,我是马仕骅,在中国音乐学院作曲系任教,是电子音乐专业方向的讲师,大家叫我老马就好。在授课之余我主要创作新媒体艺术作品,做的比较多的是视听跨媒介创作,也就是Audiovisual,呈现形式主要集中于舞台表演和装置作品两类。
音乐是我的主要背景,所以在实践这种创作的早期,声音对我来说是主导媒体,影像是作为音乐的视觉解读而存在的,用于体现声音的动态与作品结构,即所谓“声音可视化”。由于影像是更容易吸引观众注意力的媒体,为了保持音乐的主体地位,影像的元素要尽可能节省、统一,无论在为自己的音乐作品配影像,或是与作曲家朋友合作时,我都是采用这种原则来指导自己的工作。不过在创作一些更实验性的作品时,音乐不一定是其决定性作用的部分,我更重视作品的整体状态,视听、互动方式的设计是交叉进行的,就像转变不同的身份和自己合作。这种个人跨媒体创作的经验带给我更多自由,也是今后主要会持续做的方向。
是什么契机让您选择了计算机音乐与视听艺术这一领域进行深入创作?
工具带来的可能性是一方面,搞计算机音乐都会用到Max这类综合性的编程环境具备做跨媒体创作的能力,如果没有这样的高度发展的工具,当初可能不会选择这样做了。
另一方面就是个人的创作偏好了。计算机音乐是我的本行,视听艺术是外沿。我对计算机音乐的喜爱主要针对于它的创作过程,有如此多的方法可以创造和组织声音,而我可以立刻就听到它们,即使做很复杂的设计,我也能把控它的呈现结果。当计算机音乐与影像结合以后,程序里关于声音组织的一些有趣的规则可以体现在视觉上,并且随着这种结合的深入,我可以借此营造出充斥感官空间的场态,更立体地传递我想表达的内容。
在您的创作道路中,有什么经历曾经给您带来过灵感或启发?
我没有经历过什么决定性的“开窍”的瞬间......在我的体验里做这类东西靠的更多是积累,灵感或启发只能起到很少的作用。对我影响最多的其实是环境,当初在中央音乐学院求学的过程中,我陆续接触到了知识结构里的事物,形成了自己的思维方式,现在回头看是宝贵的经历。从事教师工作以后,教学让我重新思考并想清楚了很多专业上的问题,同时也在发表作品的过程中接触了更多优秀的艺术家和平台。环境在持续影响和塑造我。
您的作品《流光》中使用“流淌的光线”在数字空间内构建了视听内容,能和观众产生实时感官互动。可以为大家介绍一下这一作品的创作思路和创作过程吗?
最初的想法是想在声音装置作品中实现一种有延续性互动,让观众脱离对即时互动的关注,着重体会视听内容变化的“轨迹”,为自己的行为加入更多控制,像乐团指挥一样关注声音的呈现与自己动作的关系,这样能够创造出更具音乐性的声音装置。
为了易于体验,我希望尽可能避免让观众学习使用特殊的传感设备,因此一开始使用了深度摄像机这样的动作捕捉设备,但它们对于这个作品而言太过灵敏,我希望互动的过程放慢一些。后来找到了过去做过的一个使用光源去绘制轨迹的程序,这个程序的节奏恰好是我想要的,并且光线轨迹的图像本身就是对声音变化过程的一种视觉呈现。在作品整体设计完成之后,我又把光线轨迹的二维图像转换成了三维版本,对影像部分做了简单的加强,仅让它能通过不同的场景来体现音乐的段落结构,对声音起到辅助表现的作用。
《流光》最后产生了两个版本,首先是交互式新媒体音乐作品,有明确的结构,只由我一人控制,能更精确的还原作品的视听设计,第二个是装置版本,观众可以使用任何光源参与,包括手机背后的LED灯,互动模式比音乐版本要少,但更加直观,易于理解。
视觉和听觉传达了两种不同的感官信息,您认为二者可以产生什么样的碰撞和联系?在作品中又如何将二者进行更好结合,让观众产生联动感?
视听艺术是脱离现实却又令人信服的,从电影视听理论的角度来说,就是在构建视听幻觉。共同处在特定的语境下,当声音与影像服务于共同的表现目的时,就会趋于整合,此时如果辅助以数据上的关联,例如视听元素的空间相位、运动节奏、运动幅度等,或者更深层次的文化符号上的关联,自然能够让二者获得足够紧密的联系,也会产生很强的联动感。如果在此基础之上,能够让视听内容呈现有逻辑的结构变化,能够形成有效的艺术表达,那么二者的结合就更具意义了。
现在媒介技术手段在不断进步,“元宇宙”概念火热,未来的数字世界给人带来了无垠的遐想。您如何看待“元宇宙”这一概念? 您认为未来人和数字科技之间会发展出什么样的关系?
我认为元宇宙概念所描述的平行于现实虚拟空间是可实现的,也是被需要的。终极的人造现实是人对自己本身的超越,作为数字艺术从业者,我希望见证和参与它的每一个发展阶段,这太有吸引力了。数字科技对于未来人而言会更加无孔不入,人们甚至可以为此改造肉体接入网络,接受更真实的幻觉。对于这类情况,很多科幻艺术作品已经描绘得非常细致了,也探讨了可能会产生的一些问题,例如人机关系、伦理道德、自我认知等,这的确是可能出现的危机。一部手持的智能手机都会如此深刻的影响人的生活,当更加革新的技术出现,想必会天翻地覆了,得多屯点菜,别只顾着泡在线上。
可以透露一下您之后的创作方向和创作计划吗?
接下来还是会以视听艺术为主要的创作方向,先整理一些没有成型的作品,之后做一些和机器学习和生成艺术相关的研究和作品,希望在内容和呈现方式上做出一点个人的特色。
最后,您作为过来人,对踏上艺术创作之路的后来者有什么建议或者鼓励的话吗?
养成自学的习惯,以创造为乐趣,适当运动。
《流光》
《灵与骨》
《再声》个展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OF COURSE想当然”(ID:ofcourse_cn)。大作社经授权转载,该文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大作社平台仅提供信息存储空间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