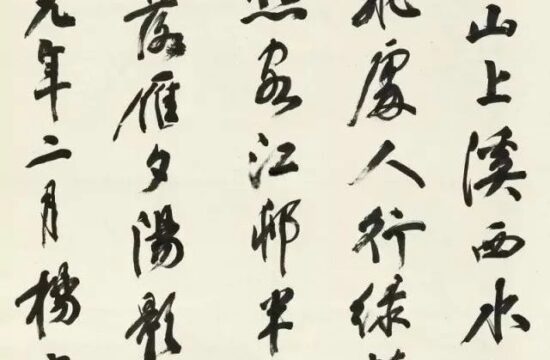Peter Joseph in studio. Photo by Rich Stapleton
Views at Peter Joseph’s studio. Photo by Rich Stapleton
Views at Peter Joseph’s studio. Photo by Rich Stapleton
Colour swatches in Peter Joseph’s studio. Photo by Rich Stapleton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Lisson里森画廊”(ID:Lisson_Gallery)。大作社经授权转载,该文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大作社平台仅提供信息存储空间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