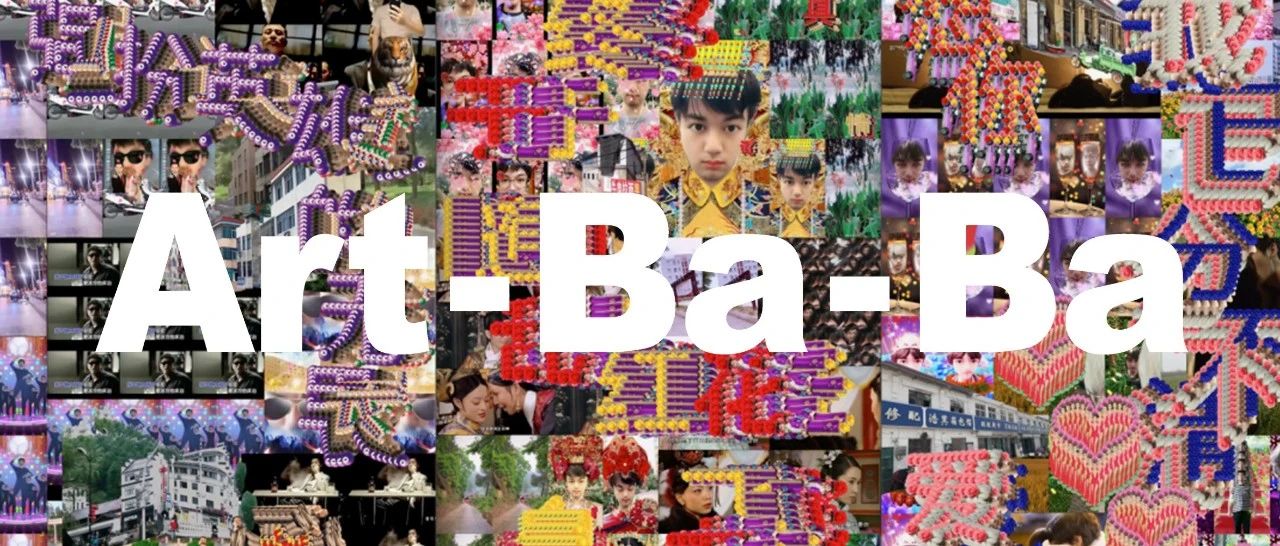⏎
“关于摄影,我对焦了某个人物,或者一片风景,调整了构图,按下了快门,于是这就是我的摄影作品,是因为我决定了在哪个瞬间按下快门吗?一个人工智能,经过机器学习,一个像素一个像素地生成了一张照片。难道它不是比我更像一个世俗意义的作者吗?作者的意义是什么?作品的意义是什么?”
采访、编辑 / 林思圻
图片致谢相关艺术家及三影堂摄影艺术中心
部分图片来源于网络
当今的摄影艺术早已不再将传统镜头视为唯一的视界,一方面作为技术发展的时代产物,伴随影像生产与传播机制的变化而不断试探和挑战图像自身的边界;另一方面则作为当下视觉艺术的重要分支,尝试发展和拓宽区别于传统摄影的艺术场域,在面对更为激进和复杂的当代生活的同时,主动介入并延伸至更为尖锐和实际的公共议题。
“集美·阿尔勒发现奖”自2015年设立以来,除了聚焦于挖掘和鼓励华人艺术家的创作和表达之外,一直致力于带动艺术研究者、策展人和创作者们共同延伸有关当下摄影艺术的讨论。本年度集美·阿尔勒发现奖单元延续往年的举办规则,邀请了5位策展人提名共计10位华人摄影师/艺术家于集美阿尔勒国际摄影季期间举办个展。今年的入围艺术家分别为:由策展人刘钢提名的张晓、李维伊;沈宸提名的陈萧伊、赵谦;祝羽捷提名的杨圆圆、袁可如;孙文杰提名的彭祖强、陈泳因;以及王懿泉提名的陈翠梅、夏诚安。马来西亚华人艺术家陈翠梅凭借展览《就因为你按了快门吗?》摘得本届集美·阿尔勒发现奖,艺术家同时获得十万元人民币奖励,并受邀前往2023法国阿尔勒摄影节举办个人展览。
陈翠梅,“就因为你按了快门吗?”展览现场,2022集美·阿尔勒国际摄影季,2022.11.25-2023.01.03
为了进一步深入当今以影像/图像为主要创作媒介的艺术家们的工作思维和方法,Art-Ba-Ba在本期内容中邀请到了“集美·阿尔勒发现奖”入围艺术家李维伊、杨圆圆、夏诚安和获奖艺术家陈翠梅,围绕他们各自在集美·阿尔勒国际摄影季呈现的展览现场,以及他们对离散群体的历史、移民文化、图像原创性和图像生成技术等具体问题的关注和研究,展开有关作为媒介的图像,图像边界以及图像叙述等话题的讨论。
Art-Ba-Ba:
相较各自以往的展览经历或工作轨迹,筹备和呈现本届集美·阿尔勒发现奖的个展过程给你们带来怎样不同的感受?你们如何围绕摄影艺术展开这次展览的构思,借助展览现场作出了哪些新的尝试?
李维伊:
这是我第一次以摄影师的身份举办展览,最大的收获便是能够有机会观察和我同龄的艺术家是如何观察世界,如何进行创作以及如何处理图像的。在这次展览“关联的图像”中,除了展出今年最新创作的《妻子们》系列之外,我选择进一步呈现我在十年前就开启的在线装置项目《家庭相册项目之二》,观众在进入展厅时能够很清晰地感知到这种用墙纸体现的集体照不仅是一种纪念碑性的图像表达,也是对集体感壮大的渴望——在我把集体照拼接成一个可以向外不断扩散的,新的集体的同时,尝试将其蔓延至其他物件的表面。这个展览关心的是,集体照是什么?为什么会出现这种视觉形式供我们选择?它们又是如何传播的?
李维伊,“关联的图像”展览现场,2022集美·阿尔勒国际摄影季,2022.11.25-2023.01.03
杨圆圆:
我设想展览空间为一个整体的剧场,展览汇集了我从2019年起至今年创作的四部纪录片:《美国亲戚》、《勿街粤曲》、《上海来的女士》以及《中国城轶事》,这些围绕个体命运的影像作品虽然是本次展览“造乡”的核心,但透过展览所呈现的摄影和档案碎片,例如作为遗物的家庭照片,或者展厅门口的舞者形象,观众可以立即看到分散影像中相互勾连的故事切片。
杨圆圆,“造乡”展览现场,2022集美·阿尔勒国际摄影季,2022.11.25-2023.01.03
夏诚安:
可能是受到芭芭拉·克鲁格 (Barbara Kruger) 的影响,她将平面设计延伸至更大的建筑空间。在这次展览“人造魅力”的筹备过程中,我也在思考如何把设计思维带入更为传统的摄影领域。可能平面设计为当代艺术领域带来的可能性并不仅仅在于图像层面,更多的是工作方法的革新,最后也并不止步于平面的图像,也有可能落实在雕塑,影像或者视频。尽管平面设计的专业训练使我能够更快速地理解文本即图像,并通过字体这个桥梁把文本和图像的表达真正联系到一起,但在完成“派对之子”杂志系列之后我便意识到,平面设计似乎不应该被局限在印刷品的面积里,那么墙纸基础上的视觉元素(科技企业的屏保图案、地产商的形象、银行logo等等)是否可以借助建筑空间,拥有自己的空间关系?或者被更进一步地放置到现实社会的语境中?
夏诚安,“人造魅力”展览现场,2022集美·阿尔勒国际摄影季,2022.11.25-2023.01.03
陈翠梅:
我向来不务正业。就算是电影,我也认为自己只是一个业余者,一个Amateur爱好者。这有时让我很尴尬,因为我总是一个“新人”。但我本身不认为这些创作属于不同领域。不论是写作、电影、摄影或者武术,都是我探索世界或思考问题的方式。我一直在持续进行的,并不是电影。比较是游戏,游戏人生的“游戏”吧?闽南语叫“蹉跎”。基本上我是蹉跎人生。你如果问我为什么会接受小泉的邀请,参与这次的展览,也真的只是我简单的觉得“这个应该很好玩”,觉得好玩的原因是,这个展览刚好是在厦门,我有很多金门的素材,一直没发表过。而且三影堂,我2018年有去过,放映电影,讲座,印象中还认真地参观了一个叫做“气”的摄影展。
陈翠梅,“就因为你按了快门吗?”展览现场,2022集美·阿尔勒国际摄影季,2022.11.25-2023.01.03
Art-Ba-Ba:
展览现场出现了大量拼贴的视觉,或重复的没有边界的图像,又或是由繁复素材堆砌形成的场景,以及不经艺术家的操纵就自主生成的照片,你们希望通过不同的视觉语言引申出有关图像的哪些议题?你们是如何思考在图像制造过程中的干预以及对图像进行的后期编辑为图像延伸出的空间?
夏诚安:
可能和我过往长期学习平面设计的经历有关,我在当时厌倦了less is more的极简设计风格,试图对平面设计的标准提出挑战。于是,在思考如何把观念可视化之外,也在思考如何从“那些不是平面设计的平面设计”出发,尝试在三维空间里进行视觉拼贴的工作。我真正感兴趣的可能不是图像所指涉的符号本身,而是符号的形成过程和传播途径,例如如何以一种意想不到的方式呈现我们日常认知中的概念,如何促成不同于以往的文本形式的研究,使符号在不同语境下呈现不同的含义和价值体系。现在有很多从事当代艺术创作的艺术家都具有很强烈的设计思维,他们擅长根据自己的视觉经验,明确推演出作品的预期,并在创作的过程中制定非常详细周密的计划,这和过往感受式的、即兴式的艺术有很明显的区别。
夏诚安,“人造魅力”展览现场,2022集美·阿尔勒国际摄影季,2022.11.25-2023.01.03
李维伊:
我们每次对图像进行处理,或者制造一个新的图像的时候,我们实际上在将自己的意图强加给世界。展览中采用的无缝图像体现了图像侵略的能力。我并不试图去创造新鲜的视觉,而是思考如何把这种力量加强,看看它最强能够到多强。就像把一只铅笔越削越尖,你可以一直削下去,直到它消失。
李维伊,《家庭相册系列二》,2022年
UV印刷,尺寸可变
图片由艺术家提供
杨圆圆:
我认为图像的叙事编织是持续开放和流动的。就像你在墙面上看到的《在一起》,我借用早期暗房技术中拼贴影像的语言,将现实生活中不能相聚的人拼贴在了一起。由于1930年代至1960年代间美国严苛的排华法案,有好几家中国照相馆运用这种拼贴的方法将被迫分离两地的家庭团聚于相纸之上。离散群体在与家乡的文化断裂中追寻自己身份的过程勾勒了海外华人的历史侧面。我一直以图集式的思维进行工作,在影像、文本和档案等不同媒介的转化间寻求讲述故事的方式,而不是面向单张的图像。另外,对纪录片进行剪辑的过程仿佛置身神秘时空的胶囊。如果在此刻再度回望过去的素材,会感觉到眼前的一切既熟悉又陌生,仍然有我数不尽的,可以挖掘的故事,它们似乎仍在询问我曾经走过的地方,即使当时手持相机的人是我,经历一切的人是我。
杨圆圆,《在一起》,2022
UV印刷,尺寸可变
图片由艺术家提供
陈翠梅:
可能是自己这几年对于“作者”和“作品”这个概念很存疑。比如拍电影,之间参与的监制,制片,编剧,导演,演员,摄影组,美术组,剪接,后期。参与的人小至30 大至300人。凭什么我可以在片头和海报上放一个“陈翠梅作品”?因为这是我的想法吗?因为我的美学判断吗?我做的决定吗?比如一块土地,我的婶婶每天在上面种菜,我的大伯公的坟墓也在这块地里面。凭什么我说这是我的土地?因为这是合法继承吗?关于摄影,我对焦了某个人物,或者一片风景,调整了构图,按下了快门,于是这就是我的摄影作品。是因为我决定了在哪个瞬间按下快门吗?一个人工智能,经过机器学习,一个像素一个像素地生成了一张照片。难道它不是比我更像一个世俗意义的作者吗?作者的意义是什么?作品的意义是什么?
陈翠梅,《两个在金门高粱地里鉴界的男人》,2022年
数字图像,由Midjourney AI生成
图片由艺术家提供
Art-Ba-Ba:
你们最初是如何关注到,又是为何选择影像/图像作为你们的创作媒介?对应其所包含的真实与虚构间的张力关系,以及艺术史中的角色变化,你们对传统摄影的看法和研究兴趣在如今发生了怎样的变化?
夏诚安:
虽然平面的图像创作并不是我唯一的媒介,但我认为传统摄影对很多观点的坚持并不重要也不必要,例如追求所谓的真实和所谓正统的工作方式,这种立场就携带着十分强烈的“我是摄影师”的执念,似乎只有使用镜头才能进行图像创作。
杨圆圆:
我自2018年起一直在拍纪录片,我意识到没有任何一种其他的方式可以像纪录片那样,如此真实地表达出讲述者在场的生命力和精神状态,它并不是为了特定的叙事而采用的媒介,而是当下必然的顺势选择。但纪录片并不是我唯一的表达工具,我从学习摄影开始我的创作生涯,后来延伸至出版、表演、影像装置等等其他媒介,所有的项目都有其多元的出口。我第一次感受到摄影带给我的强烈震撼是这张古巴革命背景下的照片。《归途》来自古巴唐人街一座华裔墓园的地下室,当我经过这片区域时,其中一个墓穴的门突然掉落,一副陌生人的遗骨和见证他过往生命历程的照片完整地暴露在我面前。这张照片生动地刻画了他曾经的形象、过去和他家人相伴在一起的场景,在古巴革命之前,他还拥有能让他维持尊严的一切。这些摄影档案和纪录片相互交织成一段难以用单一叙事概括的海外历史移民的群像记忆。除了影片中被述说出的部分,也有无法被文本或影像描述的部分,这也是拍照片和拍纪录片的意义所在,它远远超越语言,你可以从中看到故事的主人公没有表达的,以及他自己都说不清楚的感受。
杨圆圆,《归途》,2022
摄影,60 × 40 cm
李维伊:
我们现在在互联网上看到的海量图像铺天盖地,但制造图像的人,他们的立场和视角其实是被忽略,甚至是被抹去的。我认为制造图像的动机和图像本身同等的重要,所以对我来说,与其说我在研究图像,倒不如说是在研究图像背后的那个人。
李维伊,“关联的图像”展览现场,2022集美·阿尔勒国际摄影季,2022.11.25-2023.01.03
Art-Ba-Ba:
在当今艺术和技术的新型关系下,你们怎么看待不断加速更替的图像生成技术?艺术创作的方法和新兴的视觉语言对于影像媒介演变过程中图像意义的传递有哪些具体的影响?
李维伊:
图像生成技术在如今发展的越来越多元化,无论是制图工具,AI绘画、3D扫描与建模技术,还是正在走向成熟的Meta (由Facebook部分品牌更名而来) ,都在表明我们的未来注定会被包裹在虚拟的数码薄膜之中。尽管现在有很多艺术家会使用各种各样的图像技术来制造视觉性很强的作品,但我一直清楚我走在与他们相反的路径上,我希望告诉观众这个技术本身是什么,为何它具备诱惑的能力。我认为研究图像技术的责任之一就是像弗鲁塞尔所说的,应当戳穿技术,而不是变成它的吹捧者。
夏诚安:
你可以在展览现场的壁纸中看到很明显的输出错误,例如在数字屏幕中获得高清表现的照片轮廓却在输出设备受限的实际场景中呈现强烈的锯齿感,这种低分辨率的效果在周边画笔清晰锐利的路径对比下显得格外明显,甚至可能被误以为是低清意识主导下的产物。这种表现形式可能会让人联想到黑特·史德耶尔 (Hito Steyerl) 所说的“坏图像” (The Poor Image) 所指代的民间的、业余的、非专业的数据形式。但我的意图并非一味地用低清的像素来宣泄我对文化符号挪用的观点,而是去接近介于专业与业余之间的文化,就像影像作品《激光雨》中模仿土味视频的特效所作出的对流行文化同时进行“分析”和“参与”的尝试。
夏诚安,《激光雨》,2020年
网页艺术,三屏影像装置,1080P,1分钟,循环播放
图片由艺术家提供
Art-Ba-Ba:
艺术家在创作过程中有时会清晰地显现为叙述者的形象,有时作为视觉符号的一部分融入作品的表现,或者退居为隐性的第三者视角存在。艺术家的意图以及个人的艺术语言与影像创作的表达之间存在怎样的关系?
夏诚安:
无论是作为艺术家的个人形象,还是以本人的形象出现在个人的展览空间里,人物的形象都在持续经受不断被扁平化和符号化的过程,就像在展览中是如何从雕像到摄影,再到平面,再到滤镜,人物在不同的媒介中穿梭的同时越来越走向抽象。在这个过程中,个人的形象本身其实并没有那么重要,它的作用类似于展览中的线索,或者标签。相反地,我更加重视个人的形象是怎样通过不同的媒介被世界所认知,又可以通过多少种媒介被呈现出来。
夏诚安,《公摊面积》,2022年
150 × 102 cm
图片由艺术家提供
杨圆圆:
首先我不是为了特定的艺术语言进行工作的。我一直将自己视为一个讲故事的人,我的核心语言就是将镜头对向世界,希望在更长的时间轴下编织、搭建和展开与现实世界有关的叙事。纪录片的拍摄过程必然涉及人和人之间如何相处和交流,如何从相对疏离、陌生的状态转变为逐渐熟悉和亲密的关系,记录也就在这个过程期间自然而然地发生了。我相信,当人们拥有共同的目标,为了一起完成一件有意义的事情时会对彼此产生相互的信任。就像在没有项目支持、规划和预算的情况下拍摄短片《相爱的柯比与史蒂芬》和长片《女人世界》时,柯比这群年事已高的舞者愿意跟随我踏上前往古巴,再到中国的旅程,为了不再面临一次生命中的失去,我仅凭着冲动便开始了拍摄,日复一日地和时间赛跑,完全将自己融入了她们的故事。
杨圆圆,“造乡”展览现场,2022集美·阿尔勒国际摄影季,2022.11.25-2023.01.03
李维伊:
我可能并不那么关心如何发展出一套独特的,属于我个人的艺术语言,我更加关注一件事物是如何生成、又是如何被转化的,以及这一过程背后的逻辑,生产图像的人的角度和立场。
李维伊,“关联的图像”展览现场,2022集美·阿尔勒国际摄影季,2022.11.25-2023.01.03
Art-Ba-Ba:
回归到你们各自的创作路径,结合对当代艺术发展历程的认识与了解,你们认为当下对图像的讨论在不仅局限于艺术领域的情况下,还需要在哪些方面被打开?
李维伊:
对我而言,目前或许仍然只有艺术会如此坚定地欢迎我们用今天的技术去曲解过去的图像。新的解读之所以能够在艺术领域里获得实现,正是因为艺术的可能性是不被确定的,这与科学世界里充满的误解和曲解不同。我曾在一篇文学导论里看到一段关于解读作品意义的内容,大概的意思是,一件作品的意义不在作者赋予它什么样的意义,也不在于读者如何解读,而恰恰在于它能够承载意义的能力。我想这同样可以用于回应图像在当下的意义,没有任何对错,我们的工作就是把判定意义的界限打开。
夏诚安:
回到我自己的创作,我曾在某一刻突然意识到,中国的政治波普和我作品中的视觉观感存在一定程度的相似性,但我并不认为我是他们的延续。不过安迪·沃霍尔 (Andy Warhol) 对我创作的影响至今仍在作用,这一影响建立在沃霍尔从杜尚的“现成品” (readymade) 概念中跳脱出来的意识,他并没有将现成品简单的视为物品,或者视觉呈现,而是一种创作的方式方法,一种“现成品式的工作思维”,这也是我所认为的波普式创作的核心。也因此,每当我在使用特定的文化符号之前,并不会直接从现实中进行直接抽取,而是事先探究它的来源,有意识地对其剖析并明确我对这种文化进行挪用的意图,从而将其替换为我对该议题的理解。
杨圆圆:
图像在当下的时代已经非常泛滥了,“决定性的瞬间”早已过去。然而,就像影像档案为我们揭示的,我们无法想象1930年代海外的粤曲发展的如此有创造力,在电视、电影还未发明的时期,舞台不仅是结合了影视的剧场空间,也作为政治宣传的工具传递着不同地域间的文化。但关于这份珍贵遗产的研究并不全面,长期被所谓的主流文化所边缘,我所能够做的恰恰与研究历史的学者不同,我希望通过若干影像作品,来关联和梳理粤曲文化在海外是如何对离散族群的命运产生跨越代际的影响,以及如何在交流中发生碰撞、断裂,或因为语言的不可沟通所形成的误会,甚至曲解。
Art-Ba-Ba:
特定文化背景和议题下的图像表达是以何种方式,在作为承载历史的现实切片的同时,作为艺术创作的原材料,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建立自身的起点、目的和手段?能否谈谈你们对图像的观看是如何影响你们创作视角的形成?
杨圆圆:
对我来说,那些不被讲述的事情本身就是重要的。当我们此刻经过疫情,经过世界的局部战争,再去看待全球移民的问题,会发现一切历史事件的发生都是有启示性的,同时也能强烈地感受到历史一直以相似却不同的方式重复着。就像我们对所谓边缘的定义实际上也是流动的,我们无法判定我们所关注的群体在哪一层面是被边缘的,或不被边缘的,就像世界有将近一半的人口是女性,我们依然将女性叙事称之为是被边缘化的。所以,我认为我们非常有必要站在一个更广阔的时间轴,去严肃的观察、讨论和厘清我们过去曾经面对的困境。
杨圆圆,《勿街粤曲》,2022年
单通道彩色有声高清录像,20分种
图片由艺术家提供
陈翠梅:
我的父亲1947年出生于金门,在1955年跟随我的祖母下南洋,去到新加坡寻找我的祖父。接着我的祖父到马来西亚半岛东海岸彭亨州,在一个马来渔村做起渔业。我们是这个小村子里面,唯一一家华人。祖父一直都有回去台湾的想法。
陈翠梅,《散散的地》,2022年
纪录片,2分28秒,1080P,彩色、有声
图片由艺术家和大荒电影提供
李维伊:
实际上,所有今天的技术在过去都能找到思想根源及原始替代物。这是我的博士阶段研究给我的最大启示。我们现在使用的任何图像程序的任何功能都能在历史上找到它们的前身。也因此,并不存在所谓真正新的技术。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Art Ba Ba”(ID:Art-Ba-Ba)。大作社经授权转载,该文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大作社平台仅提供信息存储空间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