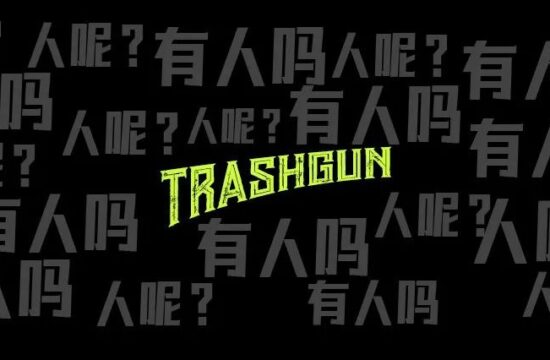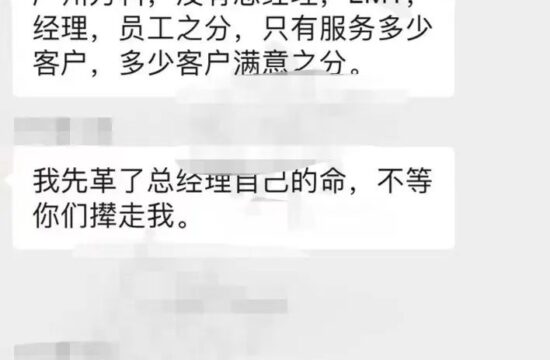每一步都踩在风口上的男人。
刘可(化名),1988年生,湖南人,35岁。2011年从建筑老八校建筑系毕业,在广州从事一线设计工作8年,2019年初从设计院裸辞,决定和妻子王悦(化名)共同开一家药店。
2019年底,新冠疫情席卷全球。
2023年初,我国终于迎来了全面放开,我们趁机采访了这个“每一步都踩在风口上的男人”。
刘可说,当时以为,从设计院辞职开药店已经是他人生中很重要的决定。而他未曾意料到随后的三年,他会经历比设想的多出很多倍的考验、困难、坚持、和价值。”
刘可回想起自己的建筑师生涯,带着一些眷念,又有些庆幸。“其实我应该算是赶上红利末期的那一波人。”
2011年毕业的刘可,因诸多原因没有选择继续深造念研究生。他当时觉得是遗憾,现在回头看,这反而让他有机会喝到时代的最后一碗汤。
千禧年的时候,我国房地产市场的供需关系的失衡开始明显显现,全国经济发展的主力城市房价开始高歌猛进,政府开始介入干预,从"国八条"到"国六条",从"调控"到"再调控",而房市尚未完全降温就迎来08年的金融危机,国家出手救市。2009年,房价就止跌回升。当年全国房价增长率达到23%左右。
这一场繁荣落到刘可身上的影响是,大三开始他就在老师的工作室兼职,身为本科生的他经常能拿到在当时相当于大部分其他专业博士的月薪。毕业后,他就顺理成章地进入设计院工作,主要承接的也都是房地产公司的住宅设计项目。工作内容重复度高、技术难度低、好处是给钱不少。
“最初报建筑学也不是出于什么梦想和追求,那都是有钱人家的孩子想的东西。我们这种穷人家的孩子,报专业的时候顶多考虑的是热门、钱多、不讨厌。”刘可笑着说:“所以我很坦然接受我的短见使我无法成为一个建筑大师。虽然加班很多,但是得到的薪水使我能养一家温饱,切实改善我们家的生活水平,已经让我很满足了。”
“再说我们也是切实解决国民需求嘛。”刘可还是笑,说这段话的时候却不看我。
2018年,房地产颓势尚未见端倪,大家都坚信政府会为这个国民经济的支柱泡沫兜底,整个建筑圈、房地产圈、甚至全国都还沉浸在房价会持续上涨的狂潮之中。而9月的时候,房企大哥万科忽然提出口号“活下去”,当时很多人觉得这个战略决策是笑话,是保守,是不想承担责任。
刘可有在万科工作的同学,也向他传达了未来几年可能整个行业都不好过的担忧。刘可说:“我觉得,房地产是我们设计院的上游行业,当源头的水冷下来的时候,上游是先感知到的。下游的鱼能做的最好的选择,就是相信上游的传话,更何况上游的大哥已经身先士卒。哪怕‘狼来了’是骗你的,也最好每次都相信,并且做好准备。”那个时候,充满危机感和财务焦虑的刘可已经开始积极寻求有没有其他职业的可能性。
到2018年底的时候,刘可因长期加班、伏案画图导致的腰椎盘突出已经愈发严重,腰椎牵引和加大口服药的剂量双管齐下也无法获得解脱。医生多次向刘可建议注意避免久坐,多注意休息,不然可能很快就要走向手术。但是“多休息”对于设计院的员工来说是一个太奢侈的词。身为药师的妻子本身就很注重身体保养,她对刘可的工作强度表达了非常强烈的不满,动不动要求刘可快点辞职。
“我媳妇的原生家庭比我好很多,所以她无法理解那种用健康换薪水的行为。我们俩对于物质生活的欲望都不高,但是我的财务焦虑比她高太多了。她总是骂我不顾家、不顾小孩、甚至不顾自己的健康、罔顾她下半辈子的幸福。”刘可说到这,看到我意味深长的目光,笑骂了一句。
“所以慢慢地我也有点被她洗脑了,将健康和家庭生活的优先级提高到赚钱之上。再加上我们也有了一些让我可以稍微安心的积蓄,以及我实在直不起腰又请不到假,辞职的计划也是写在日程里的。但是对我而言,还缺一个能让我下定决心的因素,就是我不知道我能干什么,这让我很紧张,担心断了收入来源。”刘可说这些话的时候,脸上已经没有了他诉说的紧绷感。
机会来的就是这么巧,2018年底,王悦顺利取得了执业药师证,她的一个药师同事撺掇他们小两口一起合伙盘一个药店。经过简单的收支估算,刘可认为这就是他等的那个出口、那个契机,于是在2019年初,拿到年终奖的刘可就裸辞了,休息了一个自工作以来最长的假期。
辞职后虽然不用加班了,但是踏出舒适圈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选址和装修是整个过程中刘可唯一还能称得上擅长的事情。
考虑到前期费用和后期经营管理问题,他们没有选择加盟药店,而是仗着三个人中有两个人具备专业知识和渠道,准备自己从零开始筹备一家。但开一个药店比开一个零售店多了数不清的监管,刘可也不记得那半年他们办了多少证,《药品经营许可证》、《医疗器械经营许可证》、《卫生许可证》、《健康证》、《GSP认证》、《代码证》等等,除了最初的《营业执照》和《税务登记证》是刘可自己办理的,其他都是王悦和合伙人一趟趟跑下来的。
“我是在广州这么发达的城市,可以说是全中国行政服务力最高的城市之一了,但这些事情居然没有一个是一次可以搞定的,而且大多都是我从未接触过的东西。身心俱疲的时候有时候也想答应猎头的电话回去重新上班算了,至少我已经能称自己为‘较为擅长画图了’。如果没有我媳妇的坚持和合伙人的给力,我应该最初就放弃了。”
店铺在下半年终于开业了,“像自己生了个孩子,”刘可说:“这种感觉很神奇,像第一次看着自己画的图变成拔地而起的一栋楼。”
开业初期,生意也说不上好,至少没有达到原本的预期。但好在对于选址刘可当初花了不少功夫,周边的竞争对手不多,刘可也已经慢慢上手药店的经营了。
2019年底的时候,王悦通过朋友转发的聊天记录得知了武汉的事件,当时以为只是医疗圈里的一桩谣言。而2020年1月9日,中国疾控中心徐建国院士团队向公众发布了“新型冠状病毒”的消息,王悦第一时间和刘可商量,在年前加订了一个发热及呼吸道药品的订单,备足了包含希舒美、阿莫西林、布洛芬、左氧氟沙星、枇杷膏和口罩等在内的医药用品。
随着媒体不断更新疫情变得越来越严重的新闻,店里的人流量一下子就起来了,远远超过预期,他们都是来买口罩的。考虑到非典时期的经验,他们第一时间义无反顾地下单了大量的口罩,堆满了仓库,堆到大家客厅里都挪不开脚。果然,仅仅10天的发酵,到20号的时候厂商已经不给他们供货了,网上天价口罩的消息也在疯传。国难之下,乱象丛生,有人要口罩救命,有人要口罩发财。
他们三个就蹲在在一堆口罩箱子中间开了一个会,口罩要不要涨价,要涨多少,该不该限购。
“做这几个选择真的不容易的,尤其对于一个真正穷过、还未走向富裕的人。”刘可咂巴咂巴嘴:“当时网上流传10块钱一个口罩,而你知道,我们只要卖一半的价钱,哪怕1/4的价钱,我们这一批货就可以赚到我的一年的工资。”
最后大家的决定是,小幅度涨价,每人每天限购2个,并且以药店名义给武汉捐了10箱。后来药店还是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的口罩缺货。
“说来好笑,我这么一个在乎钱的人,钱还没挣到,先把社会责任扛起来了,这算不算感动自己?”
刘可自嘲的笑却格外爽朗,我没有跟着笑。
在设计院的时候,刘可和团队最讨厌的就是客户提出各种难以满足的要求。“微信一响起我就害怕是甲方消息,无可避免很多时候我都是有些拒绝社交、又不得不回应社交的。我工作后从内心深处是更抗拒与人交流的。”
但是,“社恐”的刘可为了让附近的居民及时知道各种防疫物资的到货信息,主动开设了微信群,能随时在群里更新情况,免得大家白跑一趟,也免得大家错过采购。
2022年底,从石家庄成为第一个放开的试点城市开始,刘可他们就进入紧张状态。“这意味着中央传达了很明确的放开信息,我们仓库里的关于呼吸道、感冒、发热的药以及抗原试纸就一直按照最大囤货量在储备。我们以为是逐步放开的,谁知道感染率过高导致所有防控手段都不能得到有效成果。国家居然一下子就放开了,我们肯定是觉得很惊讶的,但是又觉得是合理的。”
全面放开的时候广州海珠的疫情都还未彻底结束,一瞬间,广州作为代表城市"全国领羊"。药物挤兑肯定是先于医疗挤兑的,首先是抗原试纸。
“那几天进店的人80%都是买试纸的,本来有的人没打算买,看到别人一袋一袋买也会忍不住买几只。原本以为核酸机构是充足的,我们试纸根本没有限购,很快就断货了。同步断货的是连花清瘟,每一个牌子都都卖空了,完全补不到货,整个国内供应商都没有,好笑的是香港的供应商说他们还有。”
“紧接着是布洛芬和对乙酰氨基酚,这两个我们反应就迅速一点,毕竟发烧是最需要警惕的症状。我们很快就下架了外卖、同时拆药卖,像古时候抓药一样,每人只能买6粒,足够撑过一个新冠周期了。但是这样还是很快卖完了存货,然后就是所有发烧药、咳嗽药都需要每天往柜上补货了。”
这个时候,刘可建立的买药群出现了大量的求助信息,刘可在有药的时候第一时间供给急需的邻里。同时,邻居们也开始自发地在群内交换或者赠送必备药品。刘可说,看到群里高频出现的“谢谢”、“感恩”、“太感谢了”之类的信息,有一种奇怪的力量涌出心头,第一次觉得自己做了一件有“价值”的事情。这样的价值感,支撑着刘可在复阴的第一时间回到了店里。这是以前在设计院从未有过的主动性,毕竟以前都是被夺命连环电话叫回去的。
我们采访刘可的时候,发现货架上一盒蒙脱石散都没有了。刘可说:“虽然明知道有些药品的抢购属实没必要,但是大家属于杯弓蛇影的阶段。”
最后刘可表示,开药店可能不是他的最终理想,因为“这只是一个买卖,没有太高的壁垒。”他正在学习相关的知识,准备找个契机投身养老行业。
刘可没有发现,他也用了理想这个词。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计成”(ID:jicheng-0102)。大作社经授权转载,该文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大作社平台仅提供信息存储空间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