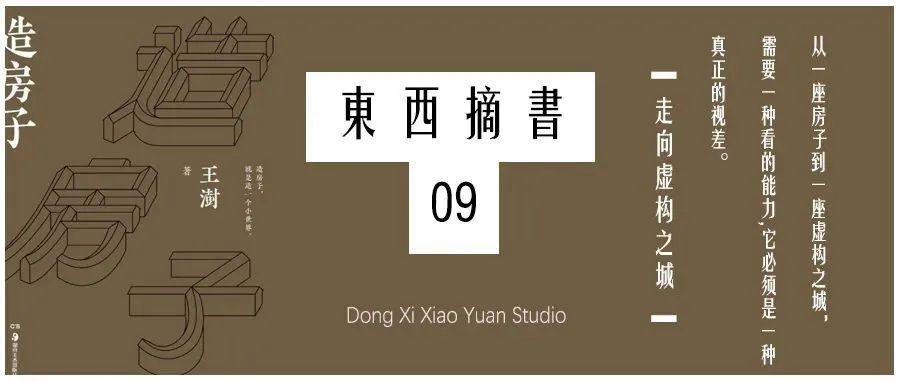这篇是摘自王澍写的《造房子》走向虚构之城 一文
时间是在去年(2002年),具体的日子记不清了。我为报考中国美术学院建筑营造研究中心的考生出了一份专业卷子。报我的考生问的第一个问题几乎都是:“实验建筑方向到底都学点什么?”我所做的就是用这个问题反问他们,只是反问的方式不同。比如,用一份卷子。写这段文字的时候,我的工作室正在搬家,一种既定的秩序被打散,打包装箱,尚未在一个新的现场被重新装配起来。那份卷子的底稿肯定在某个箱子中。
我现在写下的,是对那份卷子的回忆:
有四个人,一位哲学家,一位禅宗和尚,一位农夫(同时也是一位手工匠人,比如是铁匠或木匠),一位建筑师。某一天,他们因为某种共同的愿望或理想来到一处空旷之地,那里有一座半废弃的混凝土构筑物使他们产生了定居的欲望,于是,他们就住下来,组成一个类似合作社的组织,构筑物的空间恰好可分成四份。他们开始劳作,生活,或者冥想,从每个人所住的空间开始,而这四个空间的营造,都隐含着一座未来之城的影子。
至于学生应以何种方式完成这份卷子,除了他们需自备纸笔,我记得未做任何限制。在以后的时间里,偶尔会有朋友知道那份卷子,以为寓意深刻,我不知道该如何回答。记得是在系里,系秘书问我卷子有否拟就,中午要交上去。我就随便找张信笺,匆匆写下,这多少显得不认真,但如果意义的深度可用时间计量,那么这份卷子所说的东西我已经思考并实践了十几年了。如果一定要说从何时开始,就定在1985年吧。那年春夏,我躲在南京图书馆里看了不少书,个人意识丰富高涨,大概记得读了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宋本《五灯会元》,罗伯·格里耶的《嫉妒》,《红楼梦》(重读),索绪尔的《普通语言学教程》,一本《木工手册》,一本清人著的分析宋词格律音韵的书(只记得书名里有“梨花”二字),在一本书里初遇罗兰·巴特,还读过王朔的一篇《浮出海面》,好像刊在《收获》上,除了他后来标志性的调侃口语,刚出道的他,字里行间都透着一股生猛。
对一个个人而言,意识的自觉伴随着一个世界的诞生,尽管它可能如一个园林,是一个虚构的小世界。在那个夏天,我意识到在这个世界只有结构性的效果才能激发人的精神活力,同时也体会到“结构”一词的危险,对它所指的东西做简单化处理就显得幼稚。
过于个人化的东西,我以为不适合写在一份考卷里,事过境迁,或许可以做些补充,交代一下我在写卷子的半小时,也许是两小时里都想了什么。多年以后我才察觉,我写作,造房子,从事艺术活动,甚至生活,都以某种回忆为基础,那份卷子也是一份回忆文本,一个句子在纸上落下,就勾起一个活生生的现场情景,接着又是一个,在那份卷子背后实际上有一份类似电影分镜头剧本的东西。写哲学家时,我想的是维特根斯坦,他当过园丁,也造过房子,和他聊天时,他在给树篱剪枝;那位禅宗和尚的形象和一位农夫的形象混在一起,我曾在汉堡美术学院一位教授的工作室里看过一组幻灯,记录了20世纪80年代一位杭州郊区农夫晒谷的过程,一堵白墙前,他挑谷、撒开、翻蓐,用竹耙刮平,修出一个长方形,竹耙在谷上留下各种痕迹,一座想象之城的经脉肌理清晰可见,照片把他的动作姿态结构化了,如舞蹈,但和今天舞台上优美熟腻的所谓舞蹈不同,那是一种轻巧的小步舞,是习惯也是仪式,撒谷时就转身,于是脚腿就以不可思议的方式扭绞,如一尊罗汉;卷子里的农夫,我肯定去过他的作坊,墙上挂满工具,有一种小刨子可以放在手心里;至于那位建筑师,他造房子时,构造细节常在现场决定,而不是在图上,或许是对我自己的虚构。
这种和影像同时发生的写作或许可以解释我写东西干吗那么兴奋,写几分钟就站起来一次,在屋里转来转去,那时我已是写的东西里、造的房子里动作着的人物。我一直以为房子可以有多种文本类型的存在,至少我所想的房子,造起来行,或者不造、只拍部片子也有意思。而多文本类型的房子昭示着多种可能性的城市,它们彼此并不连缀,就像生活本身并不连缀一样。
“可能性”一词指不能预料,或者说,无法确定的契机。这个词现在被用得过滥,词义过度衰竭,听起来倒像是“必然性”,或许应用“偶然性”一词来替代。在那份卷子里,当四个人从各自所属的空间开始营造、谋划并动手,他们就走上了博尔赫斯式的彼此平行、互相交叉但永远不会相遇的道路,各自道路上的偶然性决定了一种城市的命运。你也可以说归根结底他们是在造同一座城市,但却以差异性的过程重复演绎四次。当你以看平面的视角去俯瞰这幅图景,四种城市就无可救药地重叠在一起,全无理路可言,任何理论都救不了你的命。
从一座房子到一座虚构之城,需要一种看的能力,它必须是一种真正的视差。我带学生首先带看。记得2000年5月从同济回到中国美术学院,我上的第一个班的第一堂课是在杭州吴山,半山上偶遇一堵石壁,我领着学生看了很长时间。相似性差异的石块垒在一起,它们在一起又分开,分开了又在一起。问题不在于我当时说了什么,问题在于那时刻诞生了一个没有任何先入之见的意识高涨的现场。说到“看”字,现在就一定有人搬出现象学,说要看到无人存在,只有世界本身客观呈现。但我要学生在那石璧里看见自己,看见曾经在那里的真人,这和历史文脉毫不相干。记得当年在海德格尔主持的讨论班上,有学生问海德格尔:“什么是现象学?”海德格尔一笑,看着全班说:“同学们,让我们走出教室,一起去‘现象学’地做一下。”那一时刻,外面或许正下暴雨。在无论胡塞尔写的还是海德格尔写的厚如砖头的现象学专著里,你注定啃不出个现象学来。但据说他们的课堂总是生机勃勃,即使行文木讷如胡塞尔,那种情景已经逝去,但通过某个纯粹现场,历史却可能活生生地复活。
我带学生首先带看。记得2000年5月从同济回到中国美术学院,我上的第一个班的第一堂课是在杭州吴山,半山上偶遇一堵石壁,我领着学生看了很长时间。相似性差异的石块垒在一起,它们在一起又分开,分开了又在一起。问题不在于我当时说了什么,问题在于那时刻诞生了一个没有任何先入之见的意识高涨的现场。说到“看”字,现在就一定有人搬出现象学,说要看到无人存在,只有世界本身客观呈现。但我要学生在那石璧里看见自己,看见曾经在那里的真人,这和历史文脉毫不相干。记得当年在海德格尔主持的讨论班上,有学生问海德格尔:“什么是现象学?”海德格尔一笑,看着全班说:“同学们,让我们走出教室,一起去‘现象学’地做一下。”那一时刻,外面或许正下暴雨。在无论胡塞尔写的还是海德格尔写的厚如砖头的现象学专著里,你注定啃不出个现象学来。但据说他们的课堂总是生机勃勃,即使行文木讷如胡塞尔,那种情景已经逝去,但通过某个纯粹现场,历史却可能活生生地复活。
从一座房子到一座虚构之城,需要一种看的能力,它必须是一种真正的视差。我带学生首先带看。记得2000年5月从同济回到中国美术学院,我上的第一个班的第一堂课是在杭州吴山,半山上偶遇一堵石壁,我领着学生看了很长时间。相似性差异的石块垒在一起,它们在一起又分开,分开了又在一起。问题不在于我当时说了什么,问题在于那时刻诞生了一个没有任何先入之见的意识高涨的现场。说到“看”字,现在就一定有人搬出现象学,说要看到无人存在,只有世界本身客观呈现。但我要学生在那石璧里看见自己,看见曾经在那里的真人,这和历史文脉毫不相干。记得当年在海德格尔主持的讨论班上,有学生问海德格尔:“什么是现象学?”海德格尔一笑,看着全班说:“同学们,让我们走出教室,一起去‘现象学’地做一下。”那一时刻,外面或许正下暴雨。在无论胡塞尔写的还是海德格尔写的厚如砖头的现象学专著里,你注定啃不出个现象学来。但据说他们的课堂总是生机勃勃,即使行文木讷如胡塞尔,那种情景已经逝去,但通过某个纯粹现场,历史却可能活生生地复活。
在另一天,我带学生围坐吴山上的一块大青石,喝老人茶室一元一杯的茶。周围老人成堆,打牌遛鸟,我们一共十二个人。我拿出一本福柯文集,里面有一篇讨论会记录,参加讨论的是一帮法国文人,其中或许有德勒兹‘或克里斯蒂娃?等等,也是十二个人,我要求从我开始,依序每人代表一位,把那人所说的按文序高声朗诵。那些法国文人文风晦涩又机智善辩,学生为朗诵流畅必是费了全力,其实学生读懂多少不太重要,但那一刻,思想就和身体动作重叠在一起,大家没留意的是,在周围窥视着的十二双眼睛。
“现象”不是一个平淡的词,表面的平淡隐藏着疯狂,它的呈现会让人震撼,直截了当,但未必采取激烈夸张的形式。实际上,它的出现有赖于一个纯粹主观的“人类观察者”。我的妻子总问我一个问题:“为什么在你造的房子里总有一种气氛,让人说不清楚?”我一直回答得词不达意,也许现在我有了答案。那个人类观察者隐匿在建筑看似客观的砖石梁柱间,就是说,在我造的房子里,即使只有你一个人,你以为你独占着它,但那个人类观察者已经先在,我在一篇文章里称他为X,在另一篇名为“八间不能住的房子”的文章里,我用琐碎细节勾勒过他的全部虚像。但这人类观察者永远不是一个高高在上的人,他并不俯俸,他的存在让正在发生的日常生活染上某种迷思性质。
对我来说,迷思最直接指向的即是园林,园林是迷思之地,仅此而已。2001年春,我曾带一群学生去访苏州留园,那是个熟到可以默背的园子,但其中一个院子突然间如第一次见到,也许太平常,不记得哪本书上谈过它。它实际上几乎是空的,四面白墙,半亩有余,除了院中一角一个不起眼的亭子,就是一组一组种些牡丹,用矮竹篱小心围好,大概七八组吧。我在那儿站了片刻,无话,然后对学生说:“你们一人走进一组花圃,或站或坐,随便吧。”学生们就照做,不明白原因。美院学生散漫,就有些嘻嘻哈哈,然后我说:“你们看,这就是竹林七贤。”学生们哈哈大笑,然后一哄而散,去其他有东西可看的地方做测量,画速写,完成作业。我在留园里转转,太熟,无聊,又走回有牡丹花圃的偏院,瞥见我的一位学生坐在牡丹花下看书。其后的那个上午,我又转回去两三次,那学生一直在那里,安静地看书,这学生似乎有所领悟。我站得远,不敢打扰,就有些看不清楚。也许,那学生已经睡着了,就那样在花下待了一个上午,但我看见的,是更漫长的时间从这里流过,这念头让我想起罗伯·格里耶的一段文字:
“我喜欢中国南方……它最后完全睡着了,而它那梦游者般的沉重、缓慢、颠簸着的移动却没有中断。不久,它也进入梦中,他想象水波荡漾着它的睡意……”
在那份卷子里,四个人,若问有什么共同点,那就是他们都是迷思者,除此之外,他们都是爱动手的人。定居的念头已决,就得干点什么,未必有建造一座城市的宏愿,甚至漫无目的地工作。但四个人的居所紧邻,使某种城市组织的出现并非完全出自偶然。某种空间组织总会出现,如果出现交流的欲望,则必如语言本身,从单字开始,其最小限的结构类型总是有限的。这种思考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迷思与动手并不分开,它开启了一个过程,一条道路,可能穿越体系化的知识驯养,唤醒自己面对现实的原初感觉,修复业已退化的感官。
这就是为什么我会把那样的四个人放在一起,对于可能发生什么事情,我很好奇。现在想想,这份卷子实际上是个寓言。我为什么在中国美术学院办建筑系,这系准备教什么,谁是它的教师,谁是它的学生,它将是什么样的办学机构,什么是它的学术思想,它要培养什么样的人,它可能发生的事件是否可能预测,所有的答案都在那份卷子里。它甚至回答了我为什么请未未和我一起教这个建筑系第一届学生的第一段专业课。
未未是那四个人中的哪位?也许四位都是。
我们决定一起培养造房子的人,我们都认为只教建筑没什么意思。学生毕业后一辈子只做建筑也没什么意思。与建筑相比,我们都认为房子指的东西更小,更质朴,只要你会做小房子,会造大房子就是迟早的事。当然,你可以选择只做小的,这取决于你面对世界的态度。房子还意味着你可以做其他感兴趣的事,造房子只是你的一项活动,甚至不是最主要的活动,但是,它为你打开了走进世界的一条道路。
那四个人里,我偏爱农夫,因为他做事最直接。因此第一次专业课程想让学生夯土,让这班学生为自己造一座3立方米的房子。未未建议修改教案,事先不预定材料。我说作为一个起点,需要一个原则,未未就建议用回收材料,或者说废弃材料。我说更明确地说就是不许用任何人们认为是建材的材料。未未说材料应让学生自己去选,我说这课应有一个基本原则就是老师不教,不教老师已经知道的东西,不直接教。未未说无论材料选择、造房方案、施工组织、材料采购、建造技术、预算编制、安全质量检查,所有一切,都应让学生以民主表决的方式决定。我说这个过程看似有太多不确定因素,但学生必须做出一次又一次确定的决定。这过程既开放又推动学生自觉,学会组织,挑起责任。未未说材料选择可能匪夷所思,我说不管用什么材料,解决问题的方式必须是建筑性的,是造房子,不是做装置。未未说既然造房子就应有造房子的样子,课程应从早到晚连着干,一旦开工,就应挑灯夜战,就像中国所有的土建工地一样。我说这当然让人激动,但一个简单的工程课可能就颠覆了大学的排课制度。未未说如果决定干一件事又不这样干,就没有干的必要。我说这课看上去自由,但造房子是件严格的事。未未认为不管什么材料,一旦学生投票定下来,就要严格建造质量要求,达不到要求,就让学生拆了重造。第一次这样的讨论应在2002年11月,后来又讨论了几十次,很多事记不清了。
猜测学生会选什么材料如一个游戏,结果仍出乎意料。开课三天,课堂已如废品站,不断有学生带东西进来,比如轮胎、废蓄电池壳、药用玻璃瓶、塑料可乐瓶、旧衣服、旧自行车、塑料饭盒、竹筷子、X光片、PVC管、纺纱机上的纱锭纸芯、装电脑芯片的塑料片、金属罐头盒,等等。
以后两个月的课程,大致按上面那段讨论的意思进行,其间未未从北京飞来五六次,每次待两三天,剩下的时间我就撑着。学生民主表决,决定分成四组,用四种材料。一组用自行车,一组用PVC管,一组用可乐瓶(图十三、图十四),一组用竹篾和医院里骨科拍的X光片。我们要求学生在建造前必须造出一个墙身大样,1:1的,最后的结果,只有可乐瓶组通过了验收。学生们发明了处理这种材料以及关键构造的工具,并像一支真正的施工队那样干得像模像样,但施工进度一直拖入元月,下雪天也得干,就有人叫苦。
剩下的三个组按规定并入可乐瓶组,一起干活,从挖基础开始。老师不教,学生就有点发懵,这时从农村来的孩子就有了一显身手的机会。也有些学生不甘失败,不断拿出小模型来,想说服我让他们按1∶1建造,最后自行车组索性在春节去了北京,在未未家里完成的作业,只是用的自行车全是新买的。
教学的乐趣之一就是学生提问,这个课上有两个问题让我印象深刻。课上到一半,几乎所有的学生都问我:“老师,我们什么时候开始学建筑?”又问:“老师,我们什么时候开始学设计?”问题初听让人啼笑皆非,但也没有什么过错,因为这课教的就是自发造房,和专业建筑有颠覆关系,至于“设计”一词,更是需要质疑的概念。学生如果已经明白了这些问题,他就可以毕业了。
我还记得未未在第一堂课上对学生说:“从现在开始,你们就已经毕业了,你们已经是伟大的建筑师了,因为你们将去发现问题,需要解决的问题和那些伟大建筑师每天在做的并没有什么不同。”那天上课是在西湖边上,“柳浪闻莺”,未未请全班学生喝茶,远处湖上,白堤如线,游人如点,课堂如梦。
我同意未未所说的,就像那份卷子里的四个人,当他们开始劳作、计划、造房,何曾以为自己是在学习建筑,他们所做的只是生存的一项本分工作,或者更进一步,把这本分作为感觉、梦想、虚构、玄思的对象。在课程开始,我要求学生用为自己造房子的态度去全力工作,房子造好后,全班二十五个学生每人在那间房里度过一夜,学生听了很兴奋,但半年过去,还没有学生自发地去住过。这多少让我失望,因为在我眼里,那座学生造的小房子直接指向营造的开始,设计的终结。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建筑手记”(ID:DongXiXiaoYuanStudio)。大作社经授权转载,该文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大作社平台仅提供信息存储空间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