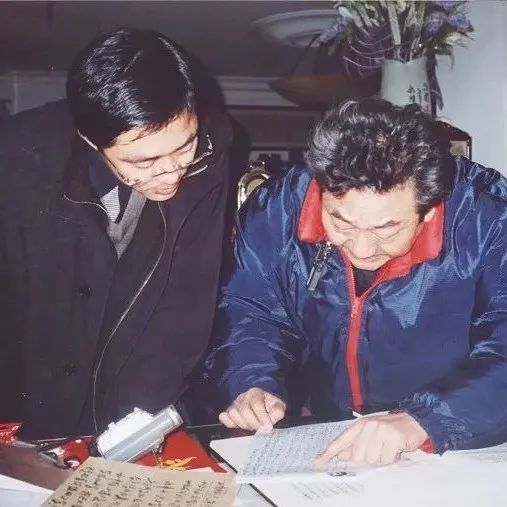艺术留学 | 论文发表 | 收藏鉴定 | 印刷出版 |
收藏合作 VX:ddms888
张公者(左)与韩天衡先生(2004年)
张公者:韩天衡先生在篆刻史上的位置是举足轻重的。明清与20世纪众多具有开拓精神的印人,几乎把篆刻创新的道路“走完了”,韩天衡先生在这种“无路可寻”中找到了自己的道路,形成奇崛雄伟、富贵堂皇、变幻多姿、精爽美妙的个人风格,并以多种篆刻面貌称雄于印史。
变则通,通则久。把握艺术语言、遵守艺术规律,则在于创造。唯有创造,才有未来,才可进入历史。历史只记载创造者。
20世纪的众多书画大师,几乎都用过韩天衡先生为其所治的印章。这是对其篆刻艺术的高度认可。韩天衡先生对印学理论的研究整理也是前所未有的。“三绝而一通”韩天衡先生的书风、画风与其篆刻风格亦达到了和谐统一。
张公者:韩老师,您为20世纪许多书画大师刻过印章。
韩天衡:这也是时代提供的机遇吧!我6岁就开始刻印, 23岁以前功夫都下在临摹秦汉印上。十几年之中前后临摹过三千多方秦汉印。就这么一本一本印谱的临、摹,有刻的,也有用笔勾摹的。我记得当时的清仪阁古印谱有张叔未收藏的四百多方印,我从头到尾全勾摹过。
张公者:您在《韩天衡印选》的后记中写道:您23岁时拿厚厚的印稿给方去疾先生看,方先生看后说您可以变了。
韩天衡:当时我还感到基本功不够。但我仔细琢磨,基本功这种东西没有止境,你就算刻到80岁基本功也不一定能过硬。我感觉,要掌握基本功,继承传统,再根据自我个性同时进行探索。方去疾先生这一席话,对我后来的探索有非常大的启迪作用。这之后我就进行这方面的探索,探索的道路是很艰难的。我的老师方介堪先生对我的探索方式非常不赞成,他认为我搞秦汉印搞得很好,为什么要“胡来”呢?陆维钊先生也是我的老师,他写信给我说:你刻的汉印,放在汉印里面足以乱真,你这样去搞,妥当不妥当呀?当时我所敬重的老前辈对我的探索,还是有一些异议的。但是我想艺术还是要独抒性灵。我记得特别清楚,当时我刻过一方图章,边款上刻了16个字:“秦印姓秦,汉印姓汉,或问余印,理当姓韩”。
张公者:这方印是在哪一年刻的?
韩天衡:是在上世纪70年代。当时方介堪先生对我寄予厚望,他看我这样探索,感觉我选择的这条路不一定对。他认为世界上的事情都是水到渠成的。上世纪70年代我正好在读一些哲学方面的书。他在温州,我在上海,我和他通过信件进行过多次辩论。我的中心思想是从来没有水到渠成的事情,总还是要认认真真、踏踏实实地把渠挖出来,水到了,就真正成为一条渠了,所以“渠成水到”。反之,你消极、被动地去“枯”等“水到渠成”,其结果往往是水不到、渠不成。当时我们有过一场带那么点哲学意义的争论。我直到现在都保留着这些信。
张公者:过去您也谈过篆刻无法做到“人印俱老”。年轻的时候就应该有自己的风貌。您是何时形成鲜明的个人风格?
韩天衡:我基本上是在1973到1975形成的个人风格,在我三十二三岁的时候。像吴昌硕,他篆刻的高峰是40岁到60岁之间,这是他印章风格最强烈、艺术内涵最丰厚的阶段。书画印这三样一般还是篆刻成熟得早。
韩天衡 葡萄青竹 70x137cm 纸本设色 2005年
张公者:您觉得是什么原因使篆刻比书法、绘画成熟得早?
韩天衡:我总结前人的经验。刻印第一个要眼力好;第二要腕力好;第三年轻时精力充沛有活力,对待作品可以反复推敲多次修改,一方印七八遍地去推敲。像我年轻的时候,一方印没有好构思,配字不妥当,石章在抽屉里面一放几个礼拜,经常拿起来反复推敲。五六十岁时还有那么多的时间和精力去推敲吗?再者,也没有这样的激情了。齐白石、吴昌硕、吴让之、赵之谦都是书画印皆能,他们的成功也是先从印里面出来的。赵之谦活了56岁,40岁以后没有刻满10方印。
张公者:吴昌硕83岁给日本人刻印,在印章的边款中说“臂痛欲裂,方知衰暮之年未可与人争竞也。”
韩天衡:吴昌硕70岁的时候讲,他不刻印已有十余年,手都生疏了。后来他刻印是比较少,而且他确实也有一些代刀人。我写过一篇文章叫《吴昌硕的代刀人》,当时我们上海的一个领导就拿这篇文章去给王个簃先生看,王个簃先生讲:这个不是事实。领导就把我叫来说:小韩,我把你这篇文章给个老看了,他说你这个不是事实。
韩天衡书法
张公者:吴昌硕晚年有些印是自己打好墨稿,由人代刻的。据您研究,王个簃先生有没有给吴昌硕代过刀?
韩天衡:应该讲,王个簃先生到吴昌硕家里时,缶老已经八十多岁了,且晚年极少刻印,他没有看到吴昌硕刻过多少印。为什么我讲吴昌硕有代刀人?因为我见过最早的资料。我年轻时读书对这方面的资料特别上心、留意。吴昌硕48岁时给吴遂初刻印,就在边上拿毛笔写着,病腕,腕痛难忍,请季仙代刻。季仙就是吴昌硕的夫人。所以吴昌硕先生的夫人是会刻印的,也就可以推论出吴昌硕起码自48岁起就开始让他的夫人和学生代刻了。这个其实并不奇怪。所以当时领导和我讲,我就说:这是吴昌硕自己讲的,我相信。
张公者: 20世纪的绘画大家李可染、陆俨少、刘海粟等都用过您的印章。
韩天衡:对,我为陆先生刻印三百多方。为谢稚柳先生刻过将近一百方。为程十发先生刻过一百多方,宋文治、徐子鹤、周昌谷,北面的可染先生、苦禅先生,还有吴作人、黄胄先生也都叫我刻过一些印。
当时我在进行一些探索,因为我感到艺术创作不能搞老一套,艺术不能搞革命,但必须要搞革新。否定传统,搞革命不符合艺术发展的规律。但是如果不改革、发展、创新,艺术的生命也就终止了。所以作为有责任的艺术工作者,必须要进行一些新的探索。上世纪70年代初期,我已经在进行探索,但很奇怪的是首先承认你的是画家。
所以有时候我开玩笑讲:佛教诞生在印度,但是后来在印度衰败了,在中国盛行了,这是个很有趣的现象。你刻印探索出一个新“腔调”,首先承认你的不是篆刻界,而是画界。圈子里的人长期以传统为是,不敢越雷池半步,总是讲字字有来历,笔笔有出处,在这样的环境里,他们就会感到你这样搞是不是这一步跨过头了。
与此相对,有成就的大画家,他首先强调的是创新,讲究个性的张扬,始终注重在传统基础上有新的探索和表现方式。他是带着一种不排斥、不泥古、不恋古的心情来看你的作品。所以虽然你的印章他们可能感到跟传统的不一样,但感觉你的新“腔调”有味道,有新的成分、新的艺术性在里面,容易获得承认。上世纪70年代,我在进行探索,正好许多画家的印章在文革当中被造反派没收了。他们看到我的印刻得很新鲜,感到有趣。画家、大师们的肯定坚定了我不断探索的信心。
韩天衡篆刻
张公者:20世纪的大家的素养都比较高,当代的画家无法和他们相比。20世纪绘画大家多数都是了不起的书法家,用印也很讲究。您和其他篆刻家不一样,能够根据各位大家的绘画风格,创作出与其画风相吻合的印章。
韩天衡:这里边有两方面。一方面,作为一个有想法的篆刻家,他必须在他的作品里表现一个“我”字,篆刻一旦为大师们所使用,它必须要注意和大师作品风格的和谐统一。这样一来,又要强调有“我”,又要强调“我”中有“你”。我当时打过一个比方,篆刻家为画家刻印,就等于是为一位高明的时装设计师设计钮扣。印章就等于衣服上面的钮扣。
它不能够随便拿来就当扣子用,它要讲究和时装设计师设计的衣服协调,尽管小,但是必须统一。所以,给画家刻印,就要解决一个有我有你的问题。如果只表现你的风格,那“我”的就没有了。如果只一味表现我的东西,不和你的相协调,也不行。这里面就涉及一个既不失他人的风格,又解决和他人协调的问题。
我给刘海粟先生刻印,我就强调一个“厚”,刘先生的作品很“重”,给刘先生刻印讲究一个“动”,灵动的动,同时也要厚。这不是一种轻薄的流动,而是一种像钢水般厚重的流动,不是像轻薄的绸带飘舞的流动。李可染先生也叫我刻过几十方印,给李可染先生刻印,也讲究厚重,但是他就不是灵动,他是一种凝练的、固定的、有分量的厚重。
给谢稚柳先生刻印要讲究雅和秀,而且这种雅和秀要表现得非常机敏。一味地只讲究自我,不讲究和别人的配合,只能做“单打选手”,不能做“双打选手”。第一,印章本身是艺术品,第二,你给画家的刻印对他来讲,需要实用和艺术相结合,你必须要作这件漂亮衣服的合适钮扣。
韩天衡 冬憩 46x47cm 纸本设色 2004年
张公者:您在自己家里刻印可以有时间思考。为李可染先生刻印,是在北京李可染先生家。在当时很短的时间里就可以考虑得很周全吗?有时间来构思吗?
韩天衡:我当时10分钟刻了3方。1方朱文、2方白文。我感到篆刻艺术和表演杂技一样,他不仅是临场表演。在无限风光的背后有辛勤的汗水和巨大的付出。我对他们的画风都比较了解,要注重平时的积累。我知道他要表现一种凝重,但不是一种流动的凝重。我给李可染先生刻印,我知道如何定位。
同样一根线条,我给陆俨少先生刻印,这根线条里要有几个微妙的摆动;我给李可染先生刻印,这根线条不好有摆动。强调一个线条的静跟动。给陆俨少先生刻的印讲动态;给李可染先生刻的印讲静态。实际上这就是一个定位和把握的问题。
我曾经和陆俨少先生开玩笑评论他和李先生的画。我说:你的画很有分量,你是摔跤冠军的那种力量,是在运动当中发力。李可染先生也是冠军,他属于举重冠军,他不是在运动当中发力,他是立在那个地方的定力。你们都是冠军,但是表现的形式又不一样。所以在刻印的时候,我就强调了一个凝固之重和飘逸之重,差别是很细微的,但是他们能体会得到。
我给李可染先生刻印,他很高兴,后来他作画都要用到我为他刻的印。刘海粟先生也很有趣的。我为陆先生刻了很多印,他拿去给刘海粟先生看。刘海粟先生一看知道是现代人刻的,认为刻得好得不得了。刘海粟先生跟陆俨少先生讲了几次,一定要叫我给他刻印。我当时不敢给他刻。
韩天衡篆刻
张公者:那是什么时候?
韩天衡:我是个党员,陆先生戴着“四顶帽子”,我和他关系极好,因为和陆俨少亲密无间,我的名字在1973年前后是上了“文攻武卫”黑名单的。刘海粟先生是一个“老反革命”,头上一大堆的帽子,又是现行反革命。
我不便去接触。陆先生就给我拿出一封刘海粟先生写给他的信,一定要我给他刻印。这样一来,我也只能硬着头皮去了。陆先生跟我交情很好,他说:刘老师一定要叫你刻印,你再不去我也不好过呀!陆俨少先生叫刘海粟先生为刘老师。在1974年陆先生就陪着我去了刘先生在上海复兴路的家,这是很有缘分的事情。
韩天衡 香生九畹 70.5cm×46cm 纸本设色 2004年
张公者:陆先生为什么称刘先生老师呢?
韩天衡:因为那时候海老和吴湖帆都属于高一辈,有威望、有影响。而且刘海粟先生和吴湖帆先生对陆俨少先生非常的器重。陆先生在解放初期已经体现出明显的个人风格,成就不一般。当时的上海,陆先生被打成右派,他觉得待在上海没劲,想到安徽去。刘海粟和吴湖帆坚决反对。所以在文革中他也和我讲:亏得我留在上海,如果我不听他们的话到安徽去,肯定第一个给打死。他要是去了,肯定是安徽的第一个绝对权威。当时安徽有一个我的师兄叫童雪鸿,也是方介堪先生的学生,文化大革命中,他在安徽也算是美术界的一个名流嘛,所以第一个就给整死了。所以陆先生很感激刘海粟。
张公者:多年前您在《光明日报》发表过一篇文章叫《感恩批评》,我拜读过。您文中提到20世纪很多大师对您的提携,对您影响最大的是哪一位?
韩天衡:我这个人最大的幸运就是碰到很多好的前辈。我未出世,我父亲的产业都给日本人炸光了,这样一来就从一个很富有的家庭,变成贫民了,而且是赤贫。我从小就喜欢艺术,很多老辈都给过我无私的帮助。我直到现在教书收学生,不收人家一分钱学费。我是以此报答我的老师。那些老师在我最穷的时候教我本事,送我笔墨纸砚、石头、刻字刀,还要送我印谱、书籍。对这些自己是没齿难忘。每一位老师都有很多东西值得你学习。比如方介堪老师对艺术的执著。他基本功扎实,一天可以刻50方印,也不写印稿,磨平了不写稿就刻,等于拿印面当宣纸,在上面任意挥洒,而且刻得非常精工、非常到位,用刀是稳、准、狠,这一点就值得你去好好学习和琢磨。比如谢稚柳老师很智慧,他是一位智者。同谢老交流可以使你对很多问题的看法,从一个一般的角度,转移到一个很新、很深的视角去理解、去观察、去思考。很早,他就对我说:要多读书,不要满足于作一个印人。所以后来我就懂得多读书,读一本书就等于为爬山多登了一个台阶。一辈子在泰山脚下走和从泰山脚下往山上爬那是不一样的。我和陆俨少先生关系非常深厚,那个时候有些老先生对我的印章泼冷水的时候,他就一直叫好,他说:别人的印章,我们上海话叫“挖出来的”,天衡的印章是真正刻出来的。很自在很随意地刻出来的,不做作的。所以当介堪先生对我的印章有很多批评的时候,他是非常支持我的。这是1972至1974年。陆维钊先生在西泠印社60周年展览大会上看到我的作品后主动写信给我说:现在书法和篆刻都非常不景气,看到你的篆刻作品,我非常兴奋,今后你如果有什么困难,尽管跟我提出来,我一定会给予你帮助。还寄自己的照片给我。后来他一直讲,天衡是我的学生,我好感动。
韩天衡 篆书杜牧《山行》 纸本
张公者:沙孟海先生当年对陆先生讲:能变化就好。您怎样看陆维钊先生的作品?
韩天衡:陆维钊先生是一位很有学问的学者,他年轻的时候做叶恭绰先生的秘书,旧社会一半学生都是拿自己的学业、成绩放到老师著作里去的。陆维钊先生帮叶恭绰先生整理了很多东西。自己就没有什么著作留下来。就像高二适先生,没有留更多的著作下来,实际上章士钊的《柳文指要》里面很多的东西都是高二适先生执笔的。陆维钊先生是一位在书法上敢于进取、敢于突破的学者,他思想不保守。
张公者:您用10年的时间形成自己的风格,我也有这种变法的经历,变法过程是痛苦的。
韩天衡:那时候我有一个很好的条件,我在部队。那时候经常到北面、南面向很多老师请教,他们看我是一个部队战士,人很诚恳,又没有什么背景,不属于什么派系,都愿意教我。我也注重学习。那些大师不仅是言教,而且是身教,使我受益匪浅。
我和黄胄先生接触,在北京他家里,他在大案子上画画,我在他对面给他刻图章。黄胄先生是一个勤奋过人的画家,他有天分但更多的是出于勤奋。除了吃饭时放下毛笔拿筷子,筷子放下就是拿毛笔,再大的官到他家里来,他也是一面画画,一面讲话,从来没有停下笔和你寒暄的。
文革当中他颈椎、手都出毛病了,手不能动了,为了能拿毛笔,他掰呀!一根一根指头地掰!我看他痛得都出汗了。然后拿笔还要不停地画。所以天才出于勤奋。我们这些后来人,能从他们每人身上学一点就不得了。当然,首先就是要尊重人家,第二要承认人家。不要像现在,谁都不信,就是“我老子天下第一”,你不承认人家,不尊重人家,你就不可能去学习他。
那些老师真的是非常真诚、爱才。生怕你学不到东西。“留一手”这些东西根本没有。当然你要很诚恳,要以心换心。我最有利的条件,那些大师画画我都见过。有些他们是背着人,不画的,但他们对我是毫无保留的。
当我拿起画笔学画画的时候,我就感到好像已经学了10年了,因为我看到过这些大师是怎么执笔、怎么用笔、怎么掭墨,怎么画画。谢老怎么画,陆先生怎么画,海老怎么画,李可染先生怎么画。这对我来讲是一笔非常珍贵的财富。写了多少本书,读了多少年也不如看他拿起笔画几笔。有很多东西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
韩天衡绘画
张公者:您能谈谈当时您看这几位作画的情形吗?
韩天衡:陆先生画画从来不构思,他画长卷是从中间往两边画。所以他以中线为准,一路这里画过来,一路那里画过去。他画的千山万壑始终充满变化。还有,他的技巧特别好,他用笔的方法不是像我们用笔是垂直的,而是前倾的,所谓的卧笔中锋,他是用卧笔的方法来画线。这是我总结的陆先生用笔的方法。实际上有很多人笔拿得笔直,这当然也是一种方法,但你笔拿直了反而没中锋。中锋的出现是通过调整出现的。
画工笔的线条,它这根线条只能够起到写形的作用。陆先生的厉害,就是线条的本身有可读性、艺术性,不因造形才有艺术性。所以有的人讲笔墨不重要,我们不去评论这个问题。但你要知道,笔墨和线条本身是有文野、优劣、高下之分的。陆先生的线条就是属于文的、雅的、高的、优的。我帮他总结过,我说:您很厉害,您用笔的时候,画细线条强调用笔尖,而且你在表现细线条的时候是笔尖里包含了一个笔肚的部分在那里。
但是单用笔尖画出的线条,它的韵律就差,笔尖加一点笔肚的线条在那里运动,第一,线条着纸的程度深了;第二,线条着纸的幅度大了。所以那根线条出来就如我们平时讲的入木三分。他用笔方法好,笔和纸接触当中产生的痕迹,就感觉厚重。所以陆先生他的细线条是飘逸而厚重。
有很多人的线条很细,你可以讲他很精工、秀逸,但你很难用洒脱和厚重来形容它。陆先生用笔讲笔性,这里一半是天分,一半是自己的探索。我曾就他同时代的几个画家的用笔方式与他用笔方式的不同之处交谈过。他说,连他自己都没有注意这件事,我的观点,他很认同。上世纪70年代,大家都有时间,平常可以一起聊得很深透。
韩天衡与老师谢稚柳(右)在书法展上
韩天衡绘画
张公者:听说李先生不在人面前画画的。您何时看到李先生画画的?
韩天衡:当时他在外交部的台基厂招待所里作画。他画画动作很慢的,而且我去了他就停下来和我聊天了。他跟我讲:“你对齐先生的印章怎么看?”我讲:“白石先生很不容易,自创了非常雄强和猛利的风格,但齐先生的印章的优点也包含着他的缺点,他舍圆就方,斜角对称,用单刀刻印,无形中减少了很多内涵的东西。”他讲:“你讲的也有道理。
齐先生是一个极有天才的艺术家,你别看他刻印好像随随便便地划几刀,画画也很简单,实际上他是一个非常非常认真的人。他还在台子上跟我举例子,齐先生如果裁了一张纸写字,他写三个字,就要停下来拿木匠的尺量,标清还有多少距离,再写一个字,还再量。认真到这个程度。就像一个木匠在作木器家具一样的,不断地拿尺子出来量。”他还讲:“齐先生绘画感特别好。”李先生是一个非常忠厚的长者。对于年轻人取得一点成绩,或者有一点点长处,他都非常褒奖。
韩天衡(右一)与程十髪(右二)等
张公者:刘海粟先生是“敢讲话”的一位大师。
韩天衡:刘先生对我也非常好。但是刘先生的性格就和李先生不一样,他始终就是“天下以我为大”。我讲一个最有趣的事情。“四人帮”粉碎后可以开画展了。上海的卢湾区开国画展,那是“四人帮”粉碎以后的第一个国画展。上海有名的画家都参加,我也画了一张荷花送去。因为“四人帮”粉碎了,到海老那里去就没有什么顾虑了。
老先生很滑稽:“啊,天衡啊!我在展览会里面看到过你画的荷花,嘿!你到底是看到过我画画啊。你看,你现在画出来的画就大不一样啦!”刘先生是一个不拘小节的人,也是一个对青年人非常无私的长者。有些人对他有很多批评。我跟他接触,感到他没有城府,是一个比较天真的长者。比如人家拿本册页给他看,他会说:“这是你祖上传下来的恽南田的册页,恽南田是常州人,我也是常州人,你知道吧?我的名气要比他大得多了”。他这个话也会讲出来,是非常有意思的。
有一次他临摹了一个石涛的长卷,他后面有一段题跋,大意是“我要跟石涛血战到底”。他说:“天衡,你看我和石涛谁画得好?”我讲:“你画得比石涛好。”他问:“为什么?”我讲:“因为你是临石涛的,构图、章法、造型都不谈。但是石涛的线条,有的时候可能还有些败笔,而你的线条真的是厚重老辣,具有张力跟拉力,所以这一点,你跟石涛血战,血战的结果是你胜。”他讲:“天衡啊!你是真的有真知灼见。”
海老很有趣的。我记得第一次陆俨少先生陪我到海老家里去,是在1974年,他还有几顶帽子戴在头上,我没有办法,他一定要陆俨少先生叫我帮他刻图章嘛!陆先生怕老师,我不去好像他没有努力。我去的那天刘海粟很开心,说:“我要刻图章。”临走的时候,刘海粟就从他那个太师椅上下来,一直送我到二楼的楼梯口。下来的时候,陆先生就跟我讲:“天衡你的待遇比我高。”我想怎么我的待遇高呢?他讲:“我每次到刘老师家里来,临走时他就太师椅上站起来说,“你走好啊”。就这样。今天居然送你到楼梯口。他从里面到外面房间大概有十几公尺的路。所以他讲,“你的待遇比我高”。陆先生有时也会来两句幽默。
韩天衡与子女因之(后右)、回之(后左)探望病中的刘海栗(1994年)
韩天衡绘画
韩天衡篆刻
陆俨少 为韩天衡所画册页跋(1975年)
刘海栗致陆俨少信函
(原文刊发于《中国书画》杂志)
喜欢 请点 在看 分享朋友圈 也是一种 赞赏
The more we share , The more we have
图文来源于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侵权必删。
点击链接开始咨询 ↑
可选专业:东洋画,创作研讨会,书法,东方美学,西洋画,东西方美术比较,美术评论,韩国美术史,雕刻,展览企划,立体造型,工艺设计。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当代美术”(ID:dangdaimeishu)。大作社经授权转载,该文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大作社平台仅提供信息存储空间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