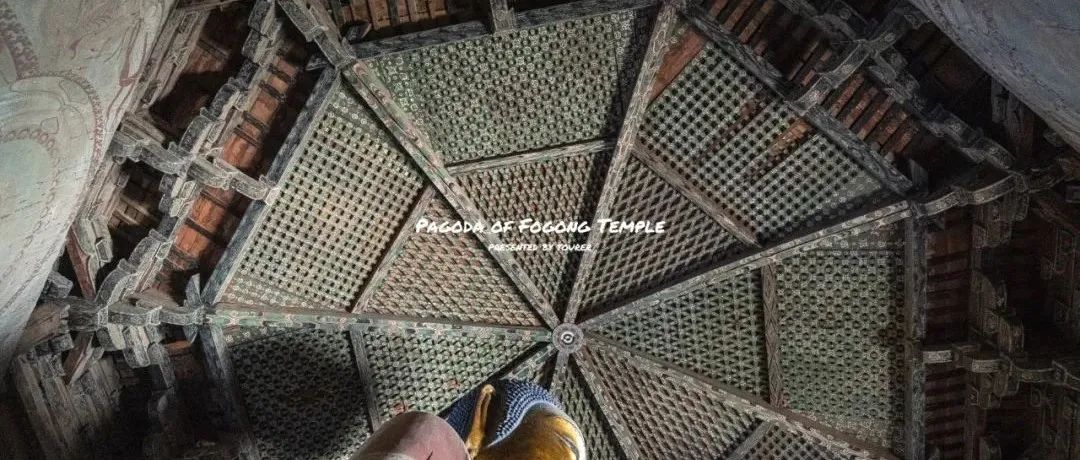途鸦er,分享旅行之美
1933年,梁思成前往应县木塔进行测绘工作,林徽因因故未能参与,梁思成便将此行全程的经历与发现事无巨细地记录下来,寄给林徽因。
我在木塔前见到过两场爱情,一场破碎,一场完满。
本文作者:最笨旅行家石头
途鸦er之人文/历史/摄影向旅行家,
《佛光寺 | “发现佛光寺,是我一生最快乐的一天”》
《龙门石窟|我看到坠落1500年的繁星亮起》
感谢你的阅读、转发和在看。
下面是1个抽奖链接按钮,3月7日晚上18点开奖,一共188元,18个红包,感谢大家的支持。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途鸦er”(ID:tuya_er)。大作社经授权转载,该文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大作社平台仅提供信息存储空间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