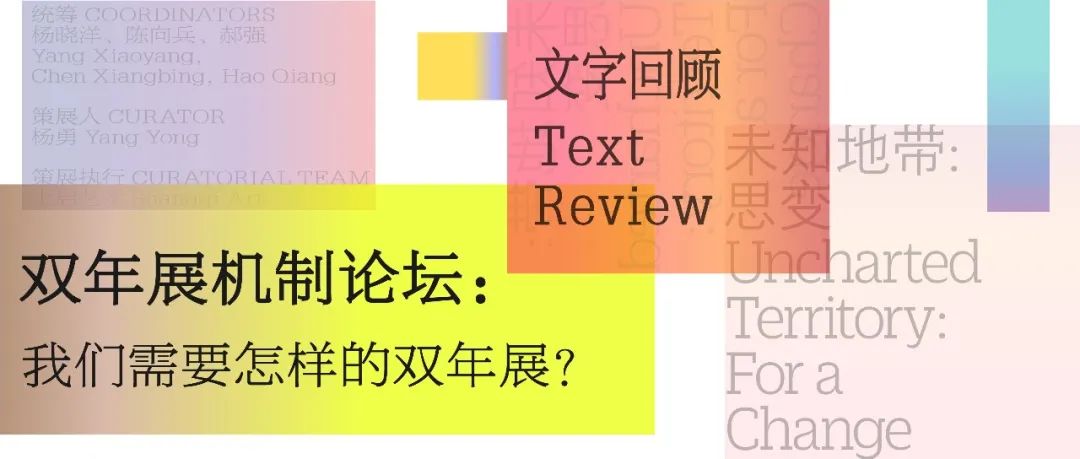“未知地带:思变——第四届深圳当代艺术双年展”以空间与实践、双年展机制、自我组织等相关专题发起闭幕论坛。“双年展机制论坛:我们需要怎样的双年展”为活动论坛。策展人、机构工作者以自身的双年展实践经验,分享对双年展机制的看法,如双年展发展模式目前遇到的挑战,对此如何改进并构建合理的艺术双年展机制,增强其有效性和公共性?如何以机制批判反思展览的构建与形成?
下为现场演讲内容节选,发布文本由上启艺术团队编辑整理,由发言嘉宾校审并提供相关图片。后续活动的演讲稿将陆续发布。
当代艺术的公共性,是一张无形的桌子
我们去年开始把双年展正式更名为“OCAT双年展”,不过OCAT双年展已经拥有二十多年的发展历史了,它的前身是我们于2012年主办的“第七届深圳雕塑双年展”,最早源起于1998年由华侨城支持,何香凝美术馆主办的“第一届当代雕塑艺术年度展”,OCAT双年展也就是从这个项目逐步发展而来。虽然前面几届展览并不以双年展命名,但对于今天OCAT双年展机制的形成,对于当代艺术的公共性/公共艺术的讨论,以及艺术实践的研究推动,都有着重要的积淀作用。
2016年我在采访当时的何香凝美术馆常务副馆长乐正维女士时,她回忆提到这个项目起初来自于时任华侨城集团副总经理陈剑先生的一个想法,当时他问何馆有没有可能在户外广场展出一些当代雕塑,与雕塑走廊连接形成互补?乐馆长认为这个想法很好,于是就找黄专老师商量,从而诞生和推动了这个项目。可以说,这个项目最早是源起于在华侨城公共空间呈现多元艺术并且希望区别于“城市雕塑”的基本想法和考虑。而从当时制定的“章程”上来看,这个项目最初是希望能够建立一种长期的、稳定的机制来推动当代艺术的发展,也试图把它打造成为一项发生在公共空间的、持续性的,具有国际性的常设性展事。它具有三个基本的特征,一是公共空间,二是当代艺术,三是时间跨度。这个项目既探讨当代艺术的公共性问题,同时强调当代艺术与在地性的关系,以及当代艺术与公众的新型关系,并且试图探索建立本土当代艺术机制。
接下来我还是以时间为线索,简单地介绍一下每届展览的基本情况。
1998年“第一届当代雕塑艺术年度展”实际上是由策展人黄专、孙振华和鲁虹老师共同策划,主要是寻找雕塑艺术切入当代的契机和发展的可能性,探讨当代艺术与公共空间的关系。当时的展场设在何香凝美术馆户外公共空间,也是美术馆早期推动当代艺术进入公共空间,探索形成“无墙美术馆”的积极实践。同期举办的“中国当代雕塑艺术研讨会”,也在尝试推动议题讨论的深化。
△ 艺术家展望早期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假山石》
2000年“第三届当代雕塑艺术年度展”由策展人易英和殷双喜老师共同策划,在之前的基础上探讨“公共艺术与文化社区”的命题,更加聚焦在艺术与社区的交流与互动。策展人提出的一个核心观点是“公共艺术的公共性以开放的社会和开放的经验为前提条件,公共空间除了具有公众自由进出的特征外,还必须具有意见的自由交流和对话的基础。”何岸的《想你,请与我联系》让艺术家与深圳这座城市和市民建立起特殊的关系,也回应了策展人和展览想探讨和实现的“自由交流和对话”的主题。
△ 艺术家何岸的装置作品《想你,请与我联系》。这件作品是在深南大道上竖起一块12米左右的灯箱广告牌,内容即标题,同时呈现艺术家的手机号。
△ 《波涛之上·地平线》,丹尼尔·布伦(Daniel Buren),2001
2003年“第五届深圳国际当代雕塑展”是由策展人侯瀚如和皮力老师共同策划,聚焦在当代艺术的公共性问题的探讨上。策展人侯瀚如老师提出的“第五系统”有意在公共艺术领域打开新的实验空间,推出针对文化语境的多样化作品,推动艺术家的实践融入城市空间的现实。在这里,艺术不只是为公众提供新的审美样式,而是让公众打开重新看待城市和思考生活的契机。策展人皮力老师则提出,“当代的公共艺术既不是艺术家对公共空间的美化,也不是一种无伤大雅的冒犯和可疑的反叛,它是无数个人叙事和公共诉求之间的双向运动。”强调的是“双向运动”的公共性。
这届展览也出现了作品进入居民日常活动的公共空间而遭遇不被理解的情况,但也有经历了很多年之后,有观众仍然回忆起对他产生影响和独具温度的作品,比如艺术家蒋志的作品《安慰洞》。也许策展人所强调的“双向运动”,正是通过这样一些方式实现。
△ 观众在《安慰洞》前与作品互动
从2007年开始,这个项目开始作为OCAT的品牌项目,由何香凝美术馆和OCAT主办。“第六届深圳当代雕塑艺术展”由策展人冯博一老师策划,提出的主题是“透视的景观”,展现的是艺术家对当下景观的体验与观察,展览希望推动艺术观念以及方法论上的改变,并呈现出丰富的视觉创造力,使观众获得新的视觉体验和感受,从而拓展当代雕塑艺术的表现空间,也推动公众对艺术新的认知和思考。
2012年,OCAT开始注册成为独立的美术馆,构建OCAT馆群,在全国布局不同学术定位的分馆。从这届展览开始,该项目正式更名为“深圳雕塑双年展”,由OCAT主办,刘鼎、卢迎华和苏伟共同策划,提出的主题是“偶然的信息:艺术不是一个体系,也不是一个世界”。策展人明确提出这是一个重提个体秩序的展览,双年展由两部分构成,一是“不期而遇的遭遇”,以1990年代作为研究对象,把艺术家个体的创作轨迹作为研究一个时代创作的基础。二是“你看到的就是我看到的”,分享了艺术家实践所建构的一种超越区域、系统、机制、规则和艺术史叙述而存在的一种“个体精神”和内在关联性。
2014年我们举办了“第八届深圳雕塑双年展”。这届双年展由马可·丹尼尔(Marko Daniel)策划,以“我们从未参与”为主题。“我们从未参与”是对拉图尔经典著作《我们从未现代过》的重复,是一种“后参与”的概念。从博伊斯的“社会雕塑”概念出发,策展人认为“艺术既是社会的,也是雕塑的;不论艺术作品变得多么的观念化、去物质化或是瞬时化,它仍然是一种物质形态”。展览仍然特别要求观众以多种不同的方式参与其中,尤其是对作品进行观察、探索和分析,或者想象性的参与,甚至是拒绝参与。
△ 《抱怨合唱团》,特雷勒沃·卡雷勒侬&奥利维·科克塔-卡雷勒侬(Tellervo Kalleinen & Oliver Kochta-Kalleinen),2014
2021年“飞去来器——OCAT双年展”,这也是OCAT首次开启“OCAT双年展”的名称,并且以馆群联动的方式推出的双年展,由OCAT深圳馆和华·美术馆联合主办,邀请冯博一老师作为总策展人,联合十一位年轻跨界的策展人,形成十个具有挑战性的展览单元。这届OCAT双年展,按主策展人的构想,是希望实现打破周期性大展容易出现的同质化的模式,从策展模式上能够有新的挑战和突破,尝试形成多方位、多触点和去策展中心化的策展实验。通过新的原则的制定,希望能够突破现有的双年展模式,摆脱单一工作模式,希望提供一种既平行又独立的新的策展可能性。而这些也是OCAT在推动双年展过程中不断思考和希望有所突破的工作方向。双年展无论是对策展人、艺术家还是机构挑战很大,但正是因为对于未知的探险,才有新的可能性的发生。
以上是基于时间顺序,简单地描述了每届展览的大致理念和基本情况,当然,早期的很多项目我其实并没有在场,也只能是通过留存下来的文献了解,很难深入描述项目本身的丰富性和多维的思想。从整个发展脉络来看,历届展览对于“雕塑”这个概念有不同的讨论和延展,随着时间的推移,也不断地推动拓展对“雕塑”的新的认知和边界。这个项目也建立起对于当代艺术的公共性的讨论和不同的探索维度。汉娜·阿伦特有一个比较生动的比喻,她把公共性比喻成一张桌子,是一个既让人们分离又是把人们联系起来的领域。当代艺术的公共性,也像这张无形的桌子一样,但我们所做的各种努力,是在尝试建立更多的对话与连接。
回到论坛的主题,我们需要一个什么样的双年展?不同的人也许会给出决然不同的答案,对于我们而言,呈现一个具有前瞻性、问题意识和研究深度,同时构建起良性的交流与对话的平台和机制,使美术馆、策展人、艺术家、作品、观众,以及为之工作的跨领域工作者,在彼此交织的双年展平台上,都能够获得彼此的启发,这是我们为之工作的其中一个重要方向。
三年展机制与城市形象
广东美术馆是中国较早创办当代艺术策展机制的美术馆,它所创办的广州三年展至今有十七、八年的历史。当时在国内除了广州三年展,还有上海双年展,这两个年展在中国当代艺术的发展轨迹里是很重要的品牌。现在国内发展出许多不同的双年展,是一个很好的现象,大家希望能通过该机制推动当代艺术的进步。
在艺术机构做学术品牌,坚守艺术理想,对于从业者来说是一个艰辛的历程。我们对历届三年展进行梳理,包括展览现场、出版书籍和衍生品等,做成学术性的文献展,展示往届对当代艺术的探索和思考,从不同的艺术话题和学术研究的角度展开讨论,让观众重新审视过去几代美术馆人的努力。除了广州三年展之外,我们还重新启动了广州影像三年展,调整三年展的框架,在结束两届影像三年展后,广州三年展即将迎来第七届,广东美术馆的新场馆也将在明年落成,今年我们希望进一步面对更多工作。
从我这几年的美术馆管理工作来看,以三年展整合资源来推动某个艺术话题的发展,是个很好的模式。每一届三年展都有反思和总结。很多人质疑三年展是否有持续的必要性,三年展是广东美术馆最重要的展览项目,可以根据学术研究、艺术家的参与程度,以及观众的反应,提高城市对艺术的关注,所以我们还在继续坚持。作为国家体系的美术馆,我们希望通过三年展,从学术研究到展览呈现为社会提供不同的艺术赏析角度,展示全新的艺术形态,让公众了解国际艺术的发展潮流、艺术家对未来的判断。因此,每一届三年展都集中了很多资源,比如人才资源,包括策展人、理论家等;比如学术资源,包括论坛和全球艺术家的作品,这体现了三年展的学术计划及其庞大的艺术生态,自然地将艺术变成城市焦点。
研究每一届双/三年展,每个地方生长的双/三年展,最关键一点是要清楚机构做双/三年展的基本定位。广州三年展有一个明确的定位,能够在中国当代艺术的生态里提出问题,有一定的学术深度,同时关注观众的观看感受,所以我们需要多方平衡,拿捏展览的基本方向。首届广州三年展在整个中国的艺术版图里相当重要,它开启了双/三年展历史的里程碑。到现在为止,我们已经发展了20年。
2002年,首届广州三年展名称为“广州当代艺术三年展”,现在已经简化为“广州三年展”。首届广州三年展的规模相当大,在整个中国的艺术版图里面十分重要,也是三年展历史的里程碑,在中国当代艺术体系里是一个划时代的展览。1990年,改革开放的初期,国际艺术思潮涌入对中国艺术产生影响,中国由此诞生了各种各样的实验性艺术,在2002年回顾中国实验艺术的十年探索,探索艺术的发展,使艺术思潮重新沸腾。展览大部分研究人员都是西方著名的历史学者和理论家,这届提出时代所反思的艺术形态。
2005年,改革开放20年,国际艺术思潮的影响深入中国,广东美术馆在第二届三年展开始寻找一些不同的实验空间进行尝试,从学术的角度寻找思考的方向。第三届广州三年展“与后殖民说再见”,是王璜生馆长在任的最后一届,当时有高世名、萨拉·马哈拉吉与张颂仁等策展人参与展览。第四届“见所未见”则是由罗一平馆长提出的学术问题推动知识生产,邀请英国伯明翰艺术设计学院教授姜节泓和英国艾康(IKON)美术馆馆长乔纳森•沃金斯(Jonathan Watkins)共同策划展览。第五届是罗一平馆长组织策划的“亚洲时间”。各届展览都挖掘了全球各地的艺术家,邀请不同的理论家、策展人一起推动展览体制的发展,与艺术家共同完成工作。
左右滑动查看图片
2018年是我到广东美术馆工作的第三年,正好接手第六届广州三年展。在广州美术学院二十多年的教学背景,以及将近十年的教学管理经验,让我对当代艺术的工作并不陌生。我们当时召开了多次意见征集的会议,向学术委员会征集了很多提案,我们收集大量资料和学者一起商议,以民主、集中的方式坚守三年展的机制。当时我们希望能够通过馆方对数字艺术与未来发展的虚拟世界展开讨论,所以提出呈现一个以数字艺术作品为主导的展览。
整个展览分为主题展和文献展,除了学术命题之外,还会面向观众普及哲学和科学的常识,通过多维的角度呈现艺术家的创作逻辑,体现艺术作品的视觉魅力。在展览筹备的过程中,我们在全球各地发掘策展人,展览主要结构由四部分组成,我们邀请了卡尔斯鲁厄艺术与媒体中心的重要策展人——菲利普·齐格勒(Philipp Ziegler),他对数字艺术有深入的研究,包括从学院的数字产业到德国卡尔斯鲁厄的城市数字媒体的完整的程度,策划了“叠加:数字中的艺术”板块。这个板块回顾迄今为止的计算机技术发展史,提出关于数字基础设施的深刻见解,展现数字对当代的渗透,预测未来数字技术发展的前景。我们也邀请了荷兰独立艺术空间MU的馆长,国际知名策展人安琪莉可·斯班尼克(Angelique Spaninks),她的知识结构相对立体,策划了“同类演化”,将技术的发明和干预带到伦理层面的探究上,将主体性延伸到非人类的生命,关注人类和非人类共同的起源和共同进化的轨迹,以及生物政治的新视野。另外一位联合策展人是中央美术学院的张尕,他大部分时间都在纽约,有丰富的国际大型展览策划经验,他在数字艺术领域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学者和策展人。他策划的“机器不孤单”进一步将主体概念延伸到非生命领域和物体世界中。通过三个部分的设置,展览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如何思考未来世界的数字技术叠加,艺术家如何探讨科技对隐私、伦理的影响,呈现出三年展的基本学术命题脉络。
而我们整个广东美术馆团队对三年展也有内容上的深度参与,着重负责文献展部分,当时我们也讨论过文献展存在的必要性,因为用三年研究一个课题,时间跨度比较长,我非常坚持的文献展环节,是因为展出的文献对观众来说会形成一个系统的观看,同时也为长期从事当代艺术研究的学者呈现了一个完整序列。最后展出的效果非常好,我们也看到许多过去参与过三年展的学者还专门回来重温当年的成果。
左右滑动查看图片
△ 第六届广州三年展文献展现场
作为广东美术馆的负责人,我希望能够有广东的艺术家参与,搭建让本地艺术家、国内外艺术家一起探讨艺术的平台。通过三年展机制我们聚集多方人才,建筑师、理论家、艺术家、策展人,结合视觉设计、媒体传播等方面,形成一个具有庞大系统和协调工作能力的展览机制。
广东美术馆有三十年历史,它的建筑结构不太适合展示当代艺术,我们也需要通过建筑师的改造让整个展场空间产生一种新鲜的“陌生感”,因为美术馆最大的问题之一在于长期进行的空间展示会让观众产生熟悉感,通过改变空间动线、色彩和灯光,能让场地给人带来新奇感。展厅的前沿性探讨也会给我们带来很多深入的思考,观众产生好奇心和求知欲来观看展览,对在展览中提出的学术问题就更能形成深刻的印象。
广东美术馆地处二沙岛,没有直达的地铁,没有停车位,交通不便,所以每次到展场的观众都是特意过来的。如果不是疫情原因,我们每天接待的观众数量几乎超负荷,尤其撤展前几天最多观众。其中有一幕场景令我很感动,当时外面下了大雨,但观众还是在广东美术馆前的广场有序排队。大家对展览热情不减,多次回访,他们踊跃地和作品互动,我们能感受到他们参观的乐趣。在展出期间,互动艺术作品《你的代码》广受观众好评。这件作品通过人工智能可以识别观众的性别、年龄和身高,观众由此和作品展开对话。数字艺术最大的魅力就是参与互动,让观众参与到作品之中。这件作品每天都站满观众,它给观众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我们最开心的是看到许多观众从艺术中得到了滋养和启发,在成长中有艺术的陪伴。作为一个国家体系的美术馆,能够为社会做实事,改变社会的艺术观念,不断提出学术问题,是我们最大的作用。
△2018第六届广州三年展现场
第六届广州三年展也为平行展设置了分展场平台。虽然资金不足,但我们也得到了企业的资助,得以把其中一个分展场设置在盒子美术馆。另外我们也有岭南美术纪念馆、华南农业大学,包括33当代艺术中心、紫泥堂艺术中心、53美术馆的分展场,在不同的展场做公共艺术的展览,邀请本地的艺术家参与其中,形成平行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我们正在筹备今年的第七届广州三年展,已确定策展人,接下来开始呈现一系列的学术命题讨论。我们也希望通过征集项目,联动大湾区的各大城市,形成城市效应,起到对区域艺术发展主要的带动作用。同时联动高校,带动各大高校的师生积极参与论坛,形成巨大的社会影响。
展览以地区命名,对于发生地来说往往是公众最期待的艺术计划。每次策划一场三年展,我们会围绕一个问题立足全国进行讨论,比如对北京、上海、成都等城市展开讨论,闭幕式也会在展场直接举办。如同深圳当代艺术双年展的闭幕式论坛,我们其实都有一个共同的目的:双年展是一个很重要的学术品牌,要办出自己的特色和学术关注点,明白责任所在,这个责任给我们带来了新的动力,希望能够通过双年展探讨我们的学术命题,同时带动整个区域艺术生态的发展。
广东美术馆为广州这座发展中的城市发声,我们也希望珠三角地区不同的城市能够参与其中,推动城市的国际化发展进程,更深入地探讨当代艺术的学术问题,面向未来,展开更多的探讨。
UABB的定位、价值与策略
深港城市\建筑双城双年展(UABB)是以城市/城市化为固定主体的综合性展览,它经过17年的发展,从2005年第一届开始,已经过去了八届,2022年即将开展第九届。目前已经成为全球最重要的建筑双年展之一,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力。展览最早由深圳市规划局发起,这种组织形式在全世界来说非常少见。UABB的命题紧紧抓住中国的城市化进程,从改革开放到今天,中国的城市化进程成为全球最关注的大事件,展览不仅关注深圳,关注中国,它也放眼全球,以全球城市和城市化研究为对象,是国际性的展览。
UABB在第一届开始设想创造超越建筑、城市,同时也超越艺术的展览,甚至可以说是制造出“城市事件”。它不仅仅是一个展览,因为它没有局限在美术馆空间里,它以整个城市为展场,从筹备到举办的过程中动员社会各界——政府规划部门、宣传文化部门,还有基层的街道办、社区,发动各行各业,比如城市研究者、建筑学家、艺术家等,同时延展到科技和其他领域,所以它是一场动员城市、凝聚共识、实验创新的社会行动。
历届UABB的展览主题以“城市”为固定标题,通过递进式的、稳定的词语结构,深度研究城市的各种可能性。它把整个城市空间和现场作为试验场,对每一位组织者、策展人、参展人来说,都是挑战极限。展览名称“深港城市\建筑双城双年展”表明着深圳和香港的联动,两座城市以同样的展览品牌各自分头组织,但是组织系统高度关联,双方各自加入对方的组委会和学委会,采用的策略也是完全一致的,通过展览在城市里的迁徙、游牧发掘城市的角落。到目前为止,在深圳和香港的展场几乎已经涉及到城市里所有的行政辖区,展览像聚光灯一样,将很多不被人关注的地方显示出来,UABB因此成了放大镜,放大城市的细节。
UABB第一届展场在OCT华侨城的厂房区域,我们在OCT华侨城创意园里连续举办了两届,第二届也是在其中。第三届转移到城市的行政中心——市民中心举办,它意味着双年展可以抵达城市的任何地方,让市民和市长共同参与双年展,对艺术体系的消解性非常有象征性。第四届设立主展场和平行展场,在市民中心的广场和OCAT举办。
左右滑动查看图片
第五届去到了城市边缘,在城市最西边的蛇口工业区选择废弃的玻璃厂,这一届的题目从城市建筑延展到社会学话题,城市边缘涉及了社会各类人群,以此研究人群跟城市空间的关系,这是UABB挑战自身的一次尝试。第六届继续延续城市边缘的体系,从城市建筑领域继续延展到城市的个体,主题叫“城市原点”,展览的对象逐渐发生了转变,从城市建筑的领域拓展到城市建筑相关的人、事、物,关注日常生活,比如当时的策展人在深圳城中村里的杂货铺拍了一张照片,让居民把带有UABB logo的袋子背上,以此制作成展览海报。
△ 2015年第六届UABB展览海报
第七届UABB更深入城中村的现场,因为深圳的城中村已经超越深圳的城市本身,成为全球化过程中非常重要的载体。在城中村里能看到全球化的各种现象,同时它又是本地特有的现象,所以这一届展览形成了非常大的影响。在城中村做展览,不仅仅是探讨跟城中村有关的话题,同时也在改变城中村的状态,让城中村去影响展览,其中包含多重的含义。这届展览的影响还在延续,因为从这届展览之后,当时的主展场南头古城进入更新阶段,改造的速度非常快,远远超过我们的想象。
△ 2017年第七届UABB展览现场 ©️UABB 摄影:张超
UABB对城市的影响可以透过华侨城创意文化园以及南头古城这两个示范性案例展现出来,发展到今天,展览产生了巨大的发酵效应,几乎所有深圳的行政辖区都开始关注UABB,展览对城市某个地区产生的带动性,成为城市发展的动力机制以及经济的发展要素,这是非常有趣的现象,它超越了展览所表达的主题内容。
第八届UABB希望挑战自身,进一步延展到其他领域。因为深圳是高科技的城市,所以我们希望这一届的主题探索科技和空间的关系,主展场之一设置在交通枢纽——福田高铁站的地下空间里,另外一个主展场则在两馆。展览主题清晰探索了技术和空间以及其未来可能性。这一届UABB讨论的领域已经超越了城市建筑,开始面向未来和科技。除此之外,展期恰好碰上疫情,人流密集的展场空间也是展览要面对的挑战。
我从三个方面总结UABB:第一是定位,展览本身已经成为以城市母体为对象的“城市行为艺术”,它不再是艺术家用表演或行为表达人的身体与艺术的关系,而是用整个展览表达城市甚至人类和地球的关系,所以这样的城市本身成为“艺术家”,双年展成为“城市行为艺术”,这是我赋予UABB的概念。因为双年展和当代艺术最大的特点就是内在的纠缠或抵抗,我们希望把内在的抵抗灌输到UABB的血液里,不希望把UABB变成平庸的、简单的、套路化的轻松展览。因为既然是在城市的母体里迁徙和游牧,它注定不会容易,它最大的敌人是自己。展览一旦标准化、套路化,变得非常光滑和好看,就表示其开始走向衰落。所以我们希望它成为自己抵抗自己的连续事件流,这是我个人对它的定位。因为UABB是涉及城市多重关系,充满复杂性的展览,所以谁也无法定位UABB,它有着很大的不确定性。
第二是价值,UABB发展到今天,已经成为可以不断挖掘、点亮、放大城市价值的“价值工厂”,具有可持续发展的潜力。如果说展览仅仅靠艺术本身,或者艺术家、建筑师本人呈现本来已经存在的东西,它的价值是有限的,而通过展览发掘、创造价值,与城市、知识系统、经济、科技关联上,展览才能由此成为传递价值的媒介,才能反过来获得社会系统的关注和支持,这也是我们未来运营UABB的目标。目前我们已经成立了UABB的基金会,希望能够获得社会各界的支持和赞助。这对于UABB的价值系统提出了很大的挑战,它潜在的价值包括模拟现实场景、直面社会痛点、活化消极地点、陌生人再凝聚、开放学习平台、批判的当代性、日常中的戏剧、临时集体部落、城市创想实验、柔性经济要素,涵盖了空间、社会、经济、艺术、科技、思想实验等等,这些生产应该是全方位的。
最后,作为面向整个城市,甚至面向全球城市的城市\建筑双年展,它需要采用多种策略,才能长期地生存,可持续地发展。所以我们希望调动整个社会的资源,让UABB与城市的发展紧紧融合在一起。我们建立了一个策略区间,UABB未来需要在四个方面塑造价值:其一是空间策略,这也是UABB作为建筑双年展吸引人的一点,因为每次展览地点都会改变,这些地方绝大多数都是城市里没有被挖掘的地点,有的是消极的城市空间,有的是待开发的空间,有的则是已经被开发的但还没完全体现其价值的地方,所以通过空间与展览匹配,让展场转化为“价值工厂”。现在整个展览采用了主展场加多个分展场的策略,希望建立空间网络,让UABB影响城市。上一届UABB的分展场已经达到9个,我们今年下半年即将开始第九届展览,目前统计的分展场同样有9个左右。它对城市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力,我们希望未来分展场会更多,这样才能够让城市空间的融合度更高。
其二是实施策略,从一开始我们非常注重双年展的实施性,展览如果仅仅是小众的人群观看,它和城市的连接会很有限。UABB作为城市双年展,它必须动员社会,跟城市里的社会机构、基层政府、基层社区进行紧密合作。UABB分展场走进社区,对策展人、参展艺术家和建筑师提出非常高的要求,通过展览这个媒介跟市民交流,让大众鉴定作品,评判双年展,甚至让作品直接走到小区,走到街道上。
其三是社会策略,当展览走到社会前沿,它对参展人、展览形态、展览方法都提出很大的挑战。以往在美术馆语境中成立的艺术品,面临着在街道、城中村、工厂中展出的问题,很多人会觉得艺术品和环境格格不入,或者艺术家也会觉得现场和作品之间不是他想象的那种关系等等。这意味着UABB必须要直接去面对城市里所有人的生存状态,特别是城市里传统意义上不被关注的人群,因为他们相当于展览的底线,如果双年展能够被他们接纳,或者反过来影响了他们,那UABB才有长久的支撑力。因为传统意义上的双年展是精英的姿态,所以现在让它走向大众,操作难度非常大。首先要改变的是我们自己。另外,还要让年轻人接受我们的双年展形态。在今年第九届里,我们特别提出了双年展的青年计划,希望通过展览为年轻艺术家、策展人和建筑师提供机会,青年的参与本身就是对UABB最大的贡献。
最后是文化策略,任何形式的双年展都要和当地的文化以及全球的文化发生对话。我们一方面要通过双年展挖掘城市里潜在的在地文化和传统文化,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通过展览塑造新的城市文化。因为像深圳这种年轻城市,它的文化还没有定型,它还在生长变化之中。这过程中UABB有责任去引领城市,去塑造城市。如果它不这样做,城市的文化会不断地衍生出我们不认识的状态,所以新的都市文化需要所有的双年展通力合作,塑造属于这一代人的新的城市文化。这对UABB,对所有的双年展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双年展不仅是知识生产,它是空间生产、社会生产、价值生产,也是文化生产。
在策展工作中看见双年展机制的当代性
2006年,我负责策划第五届深圳国际水墨双年展,主题为“水墨·生活·趣味”,我希望通过局部展示整体双年展机制,所以我将从策展角度介绍这部分的内容。当时策展的出发点是把中国的传统媒介——水墨放到当代的平台上,我提出了几个问题:为什么我当时关注的是中国传统文人的文化?在中国传统文人的语境中,水墨是很重要的成分,它成为中国文化几千年以来的模子之一,那么如何揭开模子?怎样从一个系统到另外一个系统,把水墨变成有当代意义的艺术形式?是否需要改变水墨画本身?需不需要改变我们对水墨的理解?在西方的当代艺术作品里能不能找到与中国的水墨艺术相关的共同点?我们要怎样理解水墨艺术?我们要不要从媒体和技术的角度来看待它?我们要找到它的当代质量和因素,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是我们要为水墨艺术传承提出新的理论平台和新的语境。所以我当时把展览作为理论性的平台,通过展览向观众展示不同的观看方式,比如以阅读方式可以欣赏作品、通过散步发现作品,通过互相交流作品让不同的媒体参与理论的平台。我回到中国文人的文化,中国文人文化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是“趣味”,“趣味”不是指个人喜好,而是指文人通过本身的教育,修为和在生活中产生的态度。我把这种态度称为“文人的态度”,这不仅是与文化有关的态度,也是关注社会和关注政治意识形态的态度。而另一个因素是中国水墨文化本身和理论美学,它包含注解和题跋,有比较当代的因素,比如说从视觉效果来讲,它是开放性的,很简单很直接。所以我们当时邀请艺术家解构中国水墨文化,然后再重新把它组合起来,形成新的参展作品。
△“水墨·生活·趣味——第五届深圳国际水墨双年展”展览现场,何香凝美术馆,2006
在展览入口的天井,九台风扇制造的微风吹动着九只风筝,是陈劭雄和小泽刚的作品《广州—东京II》,由风车、电风扇和风筝组成的装置作品,陈劭雄和小泽刚通过邮政快递彼此交换水墨作品,从而保持了一种远距离的艺术对话。我在作品旁边放置了像题跋一样的书法,邀请哲人和艺术家写下他们关于展览题目的想法。
其中我邀请的参展有四位艺术家,虽然他们的作品在场地中展出,但是艺术家本人有各种原因现场缺席,所以艺术家陈侗在现场搭建的工作室中创作。他在展厅里即席画出四位参展艺术家的故事,用水墨作品《缺席四条屏》介绍为什么艺术家不能到现场。
△ 《缺席四条屏》,陈侗,2006
双年展前两年我在深圳画院做了一次与水墨有关的展览,陈侗在现场画本地报纸的新闻内容,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水墨画并不是和当代的生活没有关系,它也是很有参与性的。像中国传统文人一样,陈侗不仅是艺术家,他还是政治家,行动者通过艺术表达他的意识形态和想法。
中国水墨艺术有连贯性,没有隔断,因为它一直与艺术家当下的生活环境产生关系。第五届深圳国际水墨双年展也展出20世纪初广东艺术家黄少强的作品,作品同样也是关注社会问题。
阳江组(郑国谷、陈再炎、孙庆麟)在美术馆的入口做了个卖衣服的商店,作品题目《最后一日,最后一搏》。当时阳江和深圳各地很多小商店由于各种原因倒闭,阳江组把“倒闭的小商店”作为符号,引到美术馆里表达当下的社会关注,通过民间的书写形式和买卖表达与社会有关的问题,连接着艺术和日常生活。
△ 《最后一日,最后一搏》,阳江组,2006
肖开愚用新书法的方式在展览展出他的两组手写的诗歌作品《一次抵制》,而黄少强的画和李伟铭,张志扬写的题跋和严培明的一组水墨作品《国际人造风景》也在一起展示。这也是严培明第一次用水墨实现的作品。
何香凝美术馆的建筑空间符合阅读展示,适合水墨展的需求,建筑的空间形态很丰富,大空间适合放大尺幅的作品,走廊空间适合漫步欣赏。我个人最喜欢的中国现代绘画作品是吴湖帆在1965年创作的《庆祝我国原子弹爆炸成功》。当时我没有办法从上海借到这件作品,所以我请杨诘苍作了临摹,在这里把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很重要的课题——临摹,拉进了我的展览。
在杨诘苍作品前的墙脚有一幅小素描,是阿尔及利亚裔的法国艺术家阿岱尔·阿德斯梅(Adel Abdessemed)的《原子弹避难地》,他所谓的“避难地”实际上画的是个老鼠洞。在展览的公共教育活动中,阿岱尔邀请深圳的孩子通过余东育老师在何香凝美术馆的公共项目创作“老鼠洞”的绘画图像,制造出美术馆四处都出现了“避难地”的奇景。
△ “水墨·生活·趣味——第五届深圳国际水墨双年展”展览现场,何香凝美术馆,2006
如果要谈水墨画在当代艺术上的美学,它是很直接和开放的表达。录像艺术不是规范性的纸上作品,而陈劭雄通过摄影来制作《墨水城市》里的画作,试图把水墨媒介与新兴科技形式融合起来,创作一件以传统语言讨论当代主题,参与到理论平台和语境的作品。
水墨画是很有弹性的、充满开放性的媒体,可以融入很多不同的内容,很多不同的手法和手段,实际上传达了对生活的态度,甚至模糊传统艺术和当代艺术分界。意大利艺术家组合“汕头马蹄好(Santomatteo)”参与了水墨展,而他们对水墨画本身不了解,我给他们看了八大山人画的《鹌鹑图》,引发他们创作了录像作品《花鸟山水》。
△ 《花鸟山水》影像截图,汕头马蹄好(Santomatteo)
时间关系在这里我分享的内容只是展览的局部,没有展开策略话题,我想双年展在需要大策略的同时须得关注局部。
后续活动的演讲稿将陆续发布,敬请期待!
编辑:尹余、纪浩如
设计:苏妍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上启艺术”(ID:shangqiart)。大作社经授权转载,该文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大作社平台仅提供信息存储空间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