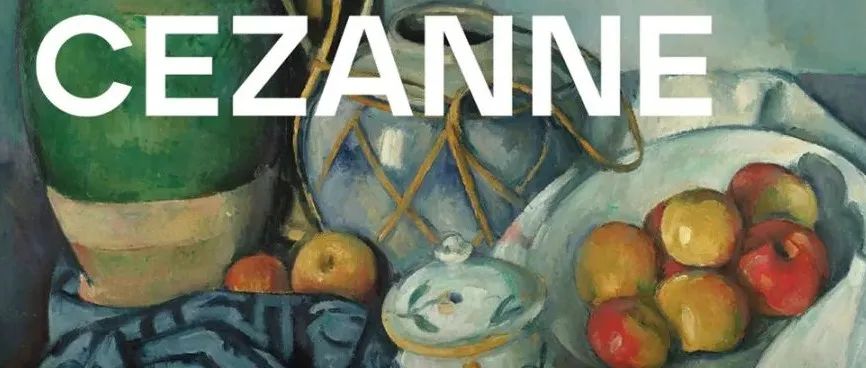芝加哥艺术博物馆近期开幕的特展“塞尚(Cezanne)”旨在追溯保罗·塞尚(Paul Cezanne)艺术语言的演变与发展,通过80幅油画、30余幅水彩作品和两本素描本,系统地呈现了塞尚成长为“现代艺术之父”近50年的历程。本篇将回溯塞尚人生的前四十载,揭开这位艺术家鲜为人知的一面。
1839年
年少踌躇时
1839年1月19日,保罗·塞尚在普罗旺斯地区艾克斯(Aix-en-Provence)出生。在他九岁时,父亲路易-奥古斯特(Louis-Auguste Cézanne)创办了一间银行,塞尚一家的生活从此由小康步入富裕。
1852年,塞尚进入波旁学院(Collège Bourbon)学习,与爱弥尔·左拉(Émile Zola)相遇。鸿鹄之志将两人牢牢牵绊在一起——塞尚渴望投身艺术,左拉则梦想成为一名优秀的作家。上学期间,他们形影不离,总在讨论如何才能在巴黎出人头地。然而,塞尚的父亲一心只想自己唯一的儿子继承家业,1859年,他安排塞尚进入艾克斯大学(Université d’Aix)学习法律。我们的艺术家没有反抗,一方面是为了安抚年迈的父亲,另一方面,他仍对自己的艺术才能抱持着怀疑。北上巴黎求学是否会是一个明智的选择?刚满二十岁的塞尚还没有找到答案。
1859年,路易-奥古斯特·塞尚买下来艾克斯附近的风之别墅(Jas de Bouffan),一直到1899年,都属于塞尚家族的财产。1880年代,塞尚在那边建立了一间工作室,常常以那边的风景为主题作画。图为他于1885年至1886年间创作的《风之别墅的栗木》,现藏于美国明尼阿波利斯艺术博物馆。
此时,左拉已朝梦想奔去,在光明之城闯荡。看到好友离成功越来越近,塞尚知道自己也不能裹足不前。他将法学院之外的时光全部花在当地的绘画学校和博物馆里,不断追求进步。偶尔感到孤独,他便会写信给左拉,字里行间充满诙谐与真挚:“你还记得阿尔克河畔那棵高耸的松树吗?它曾用自己那茂密的枝叶为我们抵挡炎炎烈日。啊,愿诸神保佑,樵夫的斧头永远不会给它致命一击!”
两年后,带着父亲的允诺和提供的津贴,塞尚启程前往巴黎。或许到生命的最后,路易-奥古斯特都未曾理解艺术令人心潮澎湃之处,但在接下来的二十余年里,他一直资助着儿子。
1861年
虔诚的探索
1861年,塞尚刚到巴黎,就被现实大泼冷水。他本以为能顺利进入学院派美术学校就读,却没通过入学考试。失意之余,他投奔苏西学院(Académie Suisse),希望能在那里迈出成为职业艺术家的第一步。这间私人工作室准入门槛较为宽松,学费低廉,颇受后来被称为“印象派”的年轻画家们欢迎。
在苏西学院的日子或许不如塞尚想象的那么如意——即便他已经得到印象派奠基人卡米耶·毕沙罗(Camille Pissarro)的认可——他很快又陷入深深的自我怀疑。来到巴黎的第五个月,他决定打道回府,在艾克斯的父亲仿佛等待已久,兴高采烈地张开双臂欢迎儿子回家。不过,事情并没有按照路易-奥古斯特预期的那样发展下去。1862年的冬天,塞尚重返巴黎。这一回,他估计真的打定主意,要在这座城市闯出一片天地。
塞尚在巴黎的第二次逗留长达8年,在艺术圈内攒了些名气,其实力却迟迟未获得官方的承认:他一次又一次向年度沙龙提及作品,一次又一次遭到拒绝。这一切并不意外,毕竟塞尚从一开始就是一个叛逆者。多数画家面对用调色刀(palette knife)作画这件事都敬而远之,但塞尚毫不忌讳。1860年代,他以近乎暴力的方式挥舞调色刀,笔触快速,完成了一件又一件作品。
假如将1872年作为时间分割点——在此之后,塞尚受毕沙罗的影响开始频繁到户外作画——那么这之前的塞尚无疑处在虔诚的探索阶段,实验各式风格,不断去卢浮宫临摹文艺复兴时期、巴洛克时期和浪漫主义时期的艺术品,研究前代大师们的艺术语言。他对调色刀的兴趣从古斯塔夫·库尔贝(Gustave Courbet,现实主义绘画代表人物)那里来,又追随欧仁·德拉克罗瓦(Eugène Delacroix,浪漫主义绘画代表人物)的步伐,以深色为基调,用厚涂塑造充满表现力的画面。
《猎狮》,欧仁·德拉克罗瓦,1860/61年,芝加哥艺术博物馆,
馆藏编号:1922.404
塞尚在这一时期的风格很难被笼统地概括为一两句话,倒是有一些特征比较稳固,比如幻想与现实世界的结合,弥漫着阴森、沉重氛围的讽刺寓言式现代场景,戏剧性的色彩对比,厚实的颜料,以及激进的笔触。他的早期作品因这些而富有活力,但也因此注定遭受沙龙的拒绝和艺术评论家的挖苦。
唯有一幅画例外。1866年,塞尚为父亲画了一幅肖像,16年后,这件作品在官方年度沙龙展出。
1872年
异乡人之间
塞尚和毕沙罗相识之后,常常相约一起画画。毕沙罗对乡村生活一往情深,大约从1865年开始,他就领着塞尚寻觅城市之外的美景。大抵是因为他们都与巴黎主流社会格格不入,两人相当投缘。塞尚是“古怪、土气的普罗旺斯人”,毕沙罗则是犹太裔,在加勒比海沿岸生活了很久。他们的性格相差甚远,但同样忤逆过父亲,也同样是坚定的反权威者。
1872年,塞尚搬去奥维尔(Auvers-sur-Oise),距离毕沙罗居住的蓬图瓦兹(Pontoise)不远。两人的合作更为频繁,塞尚迎来了创作的新阶段。他开始享受自然,学习在户外系统地工作。他还从这位年长的印象派画家那里学到了一种纪律感,并逐渐养成每日练笔的习惯。
偶尔,塞尚还是会用艺术来表现情色幻想。创作于1877年的《永恒的女性》(Eternal Feminine)和早期作品相似,带有讽刺意味。画中的裸体女性正面对来自不同阶级和行业的信徒,甚至连戴礼冠的主教都在其中,而位于画面底部的秃头人物,很可能是艺术家本人。塞尚借此作品探究女性在现代政治和社会秩序中的地位,没有清晰描绘主角的长相,也未表明她是在鼓励崇拜还是正为肆无忌惮的男性凝视所困扰。
More
1877年的几件作品可以被视为塞尚著名的“建构性笔触(constructive stroke)”的起点,他用垂直、平行和对角线的笔触加强画面秩序,统一构图。这些笔触破碎,但有别于印象派式的快速与随性。画家在对各物体的颜色和结构进行深入剖析、把握它们之间的关联后,在进行严密的计算之后,才会落下一笔。
谨慎的塞尚作画速度越来越慢,仿佛存于他骨子里的犹豫开始发酵。在他画肖像画时,这点尤为明显。他上一笔与下一笔的间隔有时长达二十分钟;曾有模特在他面前摆了一百多次姿势,只为一件作品,期间还被厉声训斥多次。无疑,要当好这位艺术家的模特,首要条件就是耐心。他的妻子玛丽-霍滕斯∙费怀特(Marie-Hortense Fiquet)恰好是这方面的“专家”。费怀特同样来自外省,19岁的时候,她和30岁的塞尚在巴黎相遇。
在1877年的这幅画像中,费怀特镇静地坐在红色扶手椅上,注视着丈夫,丝毫不怯于显示自己的威严。她的双眼炯炯有神,嘴唇紧闭,看上去有着极强的忍耐力。“你必须像苹果一样坐着!”塞尚应该无需向她发出如此指令。在她脸上斑驳的色彩呼应着衣服的蓝色和裙子的绿色,雕刻出眉毛、鼻梁和颧骨的形状,十分立体。笔触来到她的裙摆时,逐渐变得宽松、自在起来。座椅和墙面的颜色是一组对比色,为我们理清了空间的关系。曾有人这样评价:“每一块色块都在移动,它们在闪烁,它们在振动,仿佛漂浮在作品的表面。”
展览上,另一幅费怀特的肖像画更加具有纪念碑式的宏伟观感。正如他所期望的,自己的夫人坐在黄色扶手椅上,像“一座博物馆那般稳固长久”。
《坐在黄色扶手椅上的塞尚夫人》,保罗·塞尚,1888-90年,芝加哥艺术博物馆,
馆藏编号:1948.54
和印象派画家并肩同行的十年,几乎重塑了塞尚对艺术与自然两者间关系的看法。即便在那之后,在塞尚过上隐居生活的1882年之后,他也没有放下对光影的追逐,继续捕捉瞬间的视觉印象。同时,他对笔触、色彩和绘画空间的探索愈发大胆,一刻不停地思索着如何赋予所绘物象雕塑般的重量和体积,以及如何为它们变幻莫测的状态注入稳定性和永恒感。
特展:塞尚(Cezanne)
地点:芝加哥艺术博物馆Regenstein Hall
时间:2022年5月15日-9月5日
本次展览由芝加哥艺术博物馆和英国泰特现代美术馆(Tate Modern)合作举办,策展团队特别将十位当代艺术家对塞尚作品的深思融入展墙文字,引领观众审视这位活跃于19世纪的画家广泛而持久的影响力。
下期我们将聚焦塞尚人生的最后二十余年,讲述他艺术语言的进一步蜕变。
参考资料:
沈语冰,《从形式分析角度看塞尚绘画》,《书城》,2021年11月号
https://assets.moma.org/documents/moma_press-release_387094.pdf?_ga=2.41202018.1930007337.1651587175-357921376.1651587175
https://courtauld.ac.uk/highlights/montagne-sainte-victoire-with-large-pine/#&gid=1&pid=1
https://www.artnews.com/art-news/artists/paul-cezanne-who-is-he-famous-works-1234581314/
http://www.artchive.com/theory/schapiro/frame2.html
https://www.artic.edu/artworks/45240/the-bathers
https://www.artic.edu/artworks/111436/the-basket-of-apples
https://www.artic.edu/artworks/16487/the-bay-of-marseille-seen-from-l-estaque
https://www.artic.edu/exhibitions/9288/cezanne
https://www.getty.edu/art/collection/object/103RJ9?tab=bibliography
https://www.guggenheim.org/artwork/786
https://www.museothyssen.org/en/collection/artists/cezanne-paul/bottle-carafe-jug-and-lemons
https://www.moma.org/learn/moma_learning/paul-cezanne-the-bather-c-1885/
https://newcriterion.com/issues/1995/12/caczanne-at-the-grand-palais
https://www.nytimes.com/2005/06/24/arts/design/the-innovative-odd-couple-of-cezanne-and-pissarro.html
https://www.nytimes.com/2006/01/27/arts/design/finding-a-muse-in-mountains-and-chestnut-trees.html
https://www.nytimes.com/2014/12/12/arts/design/madame-czanne-at-the-metropolitan-museum.html
https://www.nytimes.com/2021/06/27/arts/design/cezanne-moma-drawings.html
https://www.nga.gov/collection/art-object-page.52085.html
https://www.oxfordartonline.com/groveart/view/10.1093/gao/9781884446054.001.0001/oao-9781884446054-e-7000015638
https://www.smithsonianmag.com/arts-culture/cezanne-107584544/
https://smarthistory.org/cezanne-mont-sainte-victoire/
https://www.theartnewspaper.com/2021/03/01/cezannes-drawings-watercolours-and-sketchbooks-to-get-star-treatment-at-moma
Rewald, John. “Cézanne and His Father." Studies in the History of Art, Vol. 4 (1971-1972): 38-62.
Schapiro, Meyer. Modern Art: Nineteenth and Twentieth Centuries. United States: G. Braziller, 1982.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芝加哥艺术博物馆AIC”(ID:ArtInstitute)。大作社经授权转载,该文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大作社平台仅提供信息存储空间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