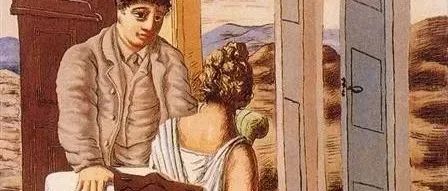注释:
*本文选自《论美术的现状——现代性之批判》,[法]让·克莱尔著,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年。
[1]Kunst kann nicht modern sein. Kunst ist urewig. 法语:L’art ne saurait être moderne. L’art revient éternellement à l’origine.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光达美术馆”(ID:guangdaart)。大作社经授权转载,该文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大作社平台仅提供信息存储空间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