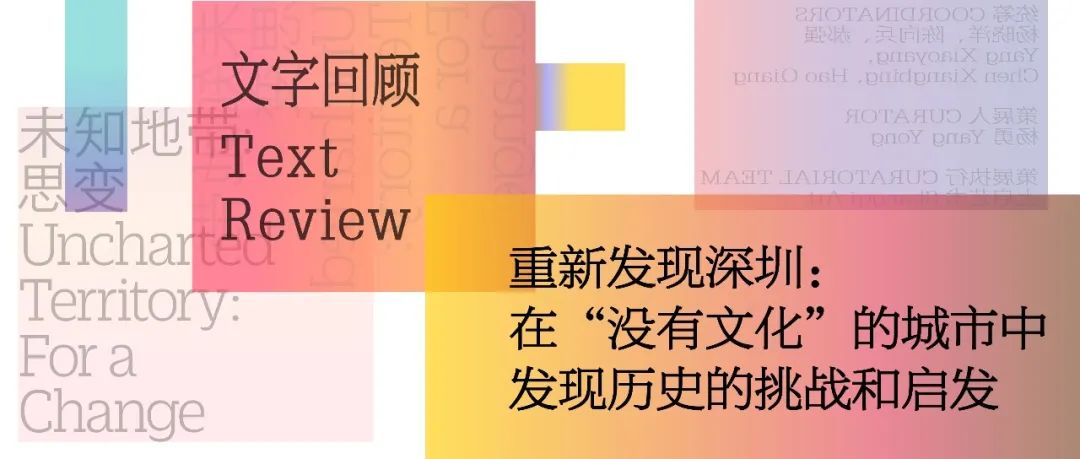“未知地带:思变——第四届深圳当代艺术双年展”以空间与实践、双年展机制、自我组织等相关专题发起闭幕论坛。“机构实践与地方文化探索”系列讲座邀请握手302的合作创始人马立安分享其机构实践。
握手302艺术空间位于深圳城中村白石洲,它将城市作为研究对象,旨在以艺术的方式探索文化地理的可能性。马立安是握手302的合作创始人,她出版的研究成果《向深圳学习》是一部全面反映深圳改革开放经验、成果及其评价的学术性著作。本次讲座中,马立安通过莱考夫和约翰逊的隐喻理论回顾握手302 进行艺术实践时所遇到的问题和解决方案。
下为现场演讲内容节选,发布文本由上启艺术团队编辑整理,由发言嘉宾校审并提供相关图片。后续活动的演讲稿将陆续发布。
在深圳,我们实践中遇到最大的挑战不是没有本地历史,而是大多数人认为本地没有历史,这也一直是“握手302”比较重要的研究方向——如何挖掘附近的意义、附近的历史、附近的启发以及未来身边的可能性。
握手302的成员有我和张凯琴、刘赫、吴丹、雷胜。我们从2012年开始在一起做事情,但我们的交流可以追溯到2010年,我和凯琴一起参与了当时的活动“发现深圳”,我和雷胜、刘赫一起参与了2011年的深港城市\建筑双城双年展,所以到了2012年我们已经互相熟悉,有一定的感情,也想做一件事情,而在这个时候我们听说了一个刺激人心的消息:白石洲要拆了。白石洲是深南大道最后一个大规模城中村,以前大规模的城中村都已经被改造,比如岗厦村和大冲村。1992年后来深圳的大多数移民是住新村,而到了2005年后,来自潮汕地区、梅县等地方的第二代移民也是住城中村,很多人的青春和城中村有关。所以对我们来说,白石洲是很多移民扎根深圳的地方,代表着深圳的人文地理和历史等方方面面。
△ 握手302工作人员合影,从左到右为:张凯琴、马立安、刘赫、吴丹、雷胜
我们在实践中一直以隐喻作为切入点。很多人以为知识是以具象存在的,其实知识存在很多人的经历和思考中,而能让这些事件和思考连到一起的,就是“隐喻”。比如,在全中国范围内都流传着一句:“食在广东”,但“食在广东”是隐喻,它是让我们通过具体的食物来理解更大范围的社会现象。所以在这个社会中,很多事物能让你产生很多联想,而联想的空间又是艺术的发挥空间,也是知识、才能扎根的空间。对深圳最根深蒂固的隐喻,是深圳从“边陲渔村”到“世界都市”的故事。用莱考夫和约翰逊的话说,“世界都市”和“渔村”都是认知隐喻,用来了解深圳。
简单地说,这两个隐喻的功能以及这两个隐喻之间的对比张力,是解释深圳的快速城市化的一个认知框架或者说是对这个认知的一种隐喻。“渔村”和“世界都市”的隐喻提供了对深圳的部分理解。
我们在当下如何理解这两个隐喻呢?其实很多现代城市都把“渔村”这个隐喻作为城市崛起的起点和神话。香港、新加坡、马来西亚都曾经是渔村,当你挖掘沿海城市背后的故事时,你会发现它们很多曾经都是渔村。
那么,渔村里的居民是做什么样的工作?它代表什么样的人文地理?香港在40年前开始现代化进程的时候,也是用“渔村”作为城市神话的隐喻,让人意识到原来这个地区曾经是如此落后。所以“渔村”让我们想象到深圳的起点是零,是贫困。但是如果你问最初的渔村在哪里?捕什么鱼?这些渔民是哪儿来的?基本上很多深圳人不知道这些问题的答案,所以“渔村”是虚指的隐喻,它是特别容易猜内容的隐喻。而另一方面,“世界都市”代表什么呢?“世界都市” 是用经济等级来描述深圳,它是高楼、建筑、金融现代化,这也是特别虚的东西。然而,这两种描述都不完整。1964年的深圳地图上显示罗湖山、深圳河,但它不是渔村,要往深圳湾方向去才会有渔村。我们在挖掘身边的历史故事的时候,其实我们是往里填充内容,把特别虚空的隐喻变得越来越丰满。
建立深圳市区前的大部分宝安县村落是位于山上的客家村落,没有直接通往海洋的码头,而许多沿海村落则以牡蛎为主要产品。深圳的渔村并不多,南头古城说官方国语,而东莞说粤语,他们住在靠珠江和靠伶仃洋的海岸。这些历史其实一直到南宋都有,深圳最老的文物在沙井,福永也有一定的历史。但它们并不是农村,那里是经营蚝业的蚝村,同时也有很多农民,唯一有水稻的最大的片区在福永。客家人聚集的山区也不是渔村,是靠河流种水稻的。海边的客家人聚居区也不是渔村,很多是出海的农民,而其他的村可能有人当渔民,但这些村庄不是渔村。所以在深圳,“渔村”一词是指1950-1957年间作为“渔业改革”运动的一部分而建立的村庄,比如渔民村、渔农村、渔一村等等。政府要求原来生活在海上的渔民上岸定居,所以渔村不是本来就有的,是改造出来的,这是建国后让渔民上岸定居工作的现代化运动后的社会现象。
“握手302”的工作重点是不断地跟民众传达:深圳渔村其实是创造出来的盲点,会让人发现不了真正的本地历史,让我们忽略本地原有的国际化元素,和发掘身边的社会和可能性的机会。深圳在龙岗、坪山有两三百年的历史,地理文化的特点是方形的客家围屋,而围屋是国际化的历史建筑。从元朝以来,深圳一直和南洋有着深厚关联,所以本土的本来就是国际化的。
我们比较受欢迎的活动是“城市走读”,活动目标是通过亲身体验不同的环境,在这些不同的环境里一边讲故事一边做艺术活动,使人意识到自己处于一个并不完全是渔村历史的语境,由此慢慢开始发现深圳的潜在可能性。如果我们一直以为深圳只是渔村,怎么去想象自己和这个城市的历史能发生什么关系?因为历史不仅是记忆,它也是我们想象未来的跳板。
△ 城市导览走读活动《城市肉体与骨骼——花园计划:华侨城模式》活动合影
位于深圳湾北岸的华侨城(OCT)片区是非常有趣的例子,因为“华侨”这个概念也是在近代历史中产生的。南洋华侨说的语言除了潮汕话之外,还有闽南语、粤语和客家话,所谓的“华侨”概念面向整个南洋,这个社群的国际历史已有几百年。如果你走进华侨城片区,你会发现“华侨农场”和“农村”也是建国后的概念,印尼、越南的华侨回国的时候,他们会被安排到农场,在农场里开始做农业。所以改革开放之初,光明的华侨农场开始进入工业领域,沙头的华侨农场开始建设工厂,这个工厂是康佳的前身,它的第一批工人是来自海南岛的华侨工厂,所以深圳整体历史是建国后现代化的历史。如果只看华侨城片区里“高大上”的住宅区,而不去看它的农业发展历史,会忽略它和南洋原有的国际联系,而国际化其实是改革开放很重要的资源,这给华侨城片区增添了很多有趣的细节。
当你走进福田的城市花园,你会发现四面是光滑的玻璃和漂亮的植物,这是我们公认的现代化,但也会发现这些环境很难和我们的身体产生关联。所以在迁徙、建楼的过程中,我们看不到当地的历史,但会发现深圳渔村的隐喻在此时发挥了作用,因为植物是迁徙过来的,人类也是迁徙过来的,最初怎么发展的问题都会集中在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城中村白石洲。因为白石洲位于华侨城片区,是华侨城的前身,此处原来拥有蚝民,因此白石洲是整个深圳的代表。
△ 《城市肉体与骨骼:福田街道办特辑—边走边吃》之“穿越未来——进入成人版的‘我的世界’”活动现场
我们在白石洲做的一个最受欢迎的关系艺术项目之一是“单身饭”。我们邀请一名“主厨”为四至六人准备一顿饭,我们提供米饭、油、调味品、碗、水和电。按每人五元的标准,主厨到白石洲购买食材,为其他参与者准备一顿饭。用餐期间,参与者分享他们在深圳定居的故事,主题提及跟深圳移民城市相关的话题,比如大多数移民的生活费用如何,迁徙到深圳后如何生活,会不会在深圳定居,要做什么才能留在深圳等等。而这些问题因为发生在有200年历史的城中村中,一个跟建国后历史有关系的地方,你会慢慢发现周边的可能性也是自己创造未来的可能性。如果只是看深圳的隐喻,会忽视掉很多可能性,包括山区的客家文化、市民中心现代化建筑的另一种可能性,甚至是城中村新移民的可能性。
后续活动的演讲稿将陆续发布,敬请期待!
本文图片为“握手302”提供
编辑:尹余、纪浩如
设计:苏妍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上启艺术”(ID:shangqiart)。大作社经授权转载,该文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大作社平台仅提供信息存储空间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