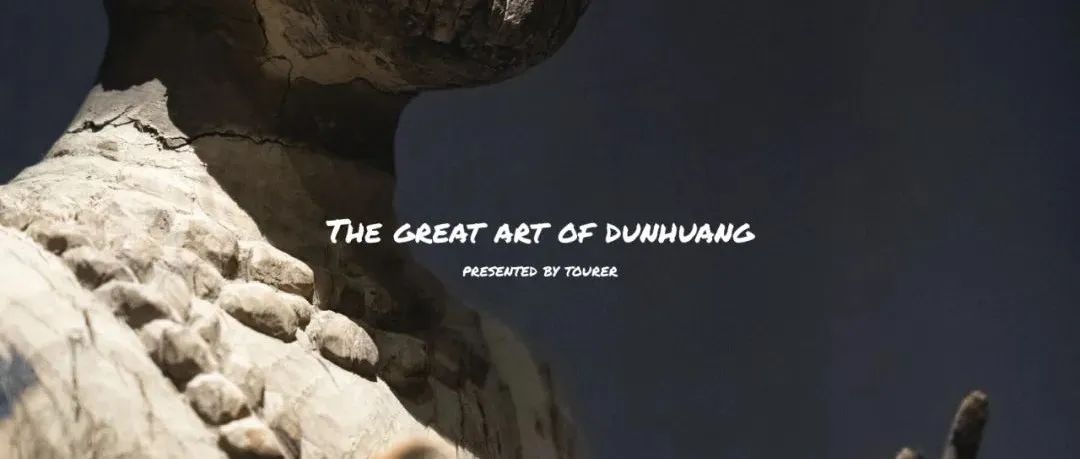途鸦er,分享旅行之美
文/图:最笨旅行家石头
主编:嗨皮不二 | 排版:往事随风
我很快被一幅不可思议的画作擒住了眼球:奇异的、瑰丽的景象,混合着色彩碰撞的恢弘巨篇,让我倒吸一口凉气。
这边眼眶中穿行着毒蛇,那边三个头的怪物嘴中爬出半个小孩。贡盘中的火焰包围着开弓放箭的白骨,小鬼撅起的臀部正喷出熊熊火柱……
《降魔成道图》:流失文物
画作中描绘的,是释迦降魔成道的场景,此类题材在敦煌藏经洞的绢画中比较少见。
佛陀结跏趺坐于画面中央,手施触地降魔印,线条迥异的头光与背光呈现出风格近似的玄幻美感;
众魔军由四面八方浩浩荡荡奔涌而来,意欲阻止佛祖成道;
佛陀头顶巨大的华盖上方,三面八臂明王现身于烈火之中;下方,造型别致的喷火小鬼格外亮眼……
全图人物繁密却有条不紊,造型极尽夸张之能事。想象力更是突破边际,释放着一种天马行空的艺术宣泄。
从健陀罗到敦煌,从云冈到麦积山,降魔成道图经历了复杂的衍变与延续,成为文化学者颇为感兴趣的话题。
降魔,不仅斩世间之恶,亦破除业障心魔。魔之愈甚,道之弥深,故对魔道大军的细致刻画,恰恰从另一面凸显了佛道的矜惜与来之不易。
如果它能在中国的博物馆里流泻自己的奇珍,该是怎样一幅场景?或者至少安静躺在藏经洞的暗夜里,而不是被禁锢在法国某个东方美术馆的橱窗中。
一场特别的展览
我将视线从它身上艰难地移开,去研究那些仍在敦煌躺着的图画。研究不过是遗忘的一种方式,但此刻的我愿意这样做。
其实,这是一段颇为不可思议的经历。原本北京的繁华被我寄望于洗刷掉之前一整年的石窟之旅所带来的烦闷,民生现代美术馆的敦煌大展却将我重新拖回了黄沙吟唱的楼兰。且原本展览是配备了专业的讲解老师的,奈何我大中午匆匆赶来,全无人影,只好一点点地啃,一缕缕地看。
先是些熟悉的面孔,如九色鹿、五台山图等。接着便是完全陌生的色彩了,竟是些并不开放的特窟!
敦煌展览常有,但大多为平面摹拓而无亲临之感。这座美术馆却完美复原了8座窟龛,甚至包括部分已经永久关闭的石窟,比如有“最美传奇洞窟”美誉的220窟,和被称为“佛教万神殿”的285窟。此外,还有俗称“卧佛像”的莫高窟最大释迦牟尼涅槃像,以及“代表大唐极致艺术”的45窟。
最终,我决定将这些人类艺术史上的珍品讲给你们听。不过且慢!在进入具体的千岁山河前,知晓两个简单概念或许大有裨益:“本生”,指佛祖释加牟尼成佛前的经历;“经变”,指佛经转变而来的画作。
它们毫无意外地指向两个主要目的:一为客观的记录,一为因果的阐述。当画作被用来描述故事或事件时,构图方式是多种多样的:从左向右、自上而下、按空间铺陈、亦或将事件发展的各个阶段全部塞入图片之中。因而,若是没有提前功,想必是极难直接看懂的。
莫高窟45窟:最美唐塑
对于美的赏析千人千面,但莫高窟45窟几乎得到了一个共同的评价:敦煌最美的唐塑。而且在莫高窟大部分彩塑于清朝重绘的背景下,这座窟保留了原汁原味的唐塑,艺术价值可见一斑。
窟龛正中,一佛二弟子二菩萨二天王呈对称排布。他们或颔首冥思,或聆听佛语,或俯查万物,或睚眦警戒,动静结合,文武兼备,造成了强烈的对比。
正壁敞口龛顶绘释迦多宝说法图,各塑像背后的龛壁和龛顶绘八弟子、诸菩萨、天龙八部和飞天等,在局促的空间中创造了层次丰富、虚实结合的气韵,堪称神笔!
莫高窟158窟:最大涅槃佛
这座永久关闭的窟龛中,藏着莫高窟最大的一尊卧佛。
身长15.8米的唐代巨佛神态安详,侧卧在1.43米高的佛台上,气定自若,毫无即将涅槃的痛苦与恋世之情。大佛脚边,塑有过去佛迦叶坐像,头侧则为未来佛米勒立像,与大佛一道构成竖三世佛像。
背后,两幅冲击力十足的《哀悼图》爬满窟壁,画中国王们有的割鼻、割耳,有的剖腹、刺胸,极度的悲痛弥漫在大佛四周,与佛本身的泰然自若形成鲜明对比。
值得注意的是,这座窟的大佛是男性与女性罕见的完美结合!
施加牟尼是男性无疑,这尊塑像却做了女性化的处理。圆润丰腴的肌体曲线,游走在轻薄如翼的袈裟下,活脱脱一位梦中少女的形象。
莫高窟285窟:绚丽至极的“万神殿”
它是莫高窟早期石窟中内容最丰富、画面最绚烂的一个,同时也是敦煌最早有确切开凿年代的洞窟,凿于西魏。另外,它也是一座永久关闭窟龛。
这里是文化汇流的结点,是古代文明唯一的聚落。
窟龛壁画中,除了佛教诸神与飞天外,还有中国早期神话中的女娲、伏羲,《山海经》中的神兽开明、乌获,道教的雷神,婆罗门教诸神,甚至西方的太阳神等,可谓各类题材的“大杂烩”。
敦煌石窟中最早、最有趣的因缘故事画《五百强盗成佛图》也出自此窟。
它简直就是一整幅连环画了!画中描绘的是古代南印度侨萨罗国,有五百强盗打家劫舍、无恶不作,最终被国王俘获。他们被施以酷刑后投至野外,痛哭哀号声不绝于耳。
佛祖闻之,以灵药救下他们,并传授佛法,收为佛教弟子,终成五百罗汉。真可谓“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莫高窟220窟:大宋剥离出的盛唐胡旋舞
1944年,莫高窟220窟壁画出现脱落,竟露出了年代更久的色彩。经过剥落,内层精美绝伦的初唐壁画赫然在目。
这也是座永久封存的窟龛。窟龛面积极大,南北壁画均为通壁巨制。
其中北壁为《药师经变》。
药师七佛下,宏大的乐舞场景占据了画面的三分之一,描绘的或许就是长安城上元夜的大型灯会。舞人的舞姿,被大部分学者认定为大唐著名的“胡旋舞”,这也是迄今为止年代最早的经变乐舞图。
《药师经变》
《药师经变》局部——胡璇乐舞
南壁上,是场景异常宏大的《无量寿经变》,为此类经变的代表之作。
《无量寿经》被誉为净土群经之首,是净土宗公认的根本佛典。壁画中,碧波荡漾的七宝池盛开着莲花,“不鼓自鸣”的飞舞乐器合奏出十方世界的妙音,无量寿佛左右群佛环绕,共同构成安乐国的种种庄严。
《无量寿经变》
较小的窟内东壁上,一幅气宇轩扬的《帝王听法图》并未被南北两壁的巨幅壁画盖过风头。
这幅画与唐代大画家阎立本的《历代帝王图》形制颇为相似,但无论是年代之早、人物之多、场面之盛、元素之丰都远超后者,可谓超越时代的珍宝。
《文殊问疾》之《帝王听法图》
旋转腾跃的胡旋舞人,在昏暗的石窟中舞动出一个丰腴时代未曾远去的光彩。仿佛那场千年前的盛会,依旧在古老大地的某个角落,震颤出苍茫的余音。
《都督夫人礼佛图》:丰腴盛唐的绝响
盛唐的这份丰腴之美,在《都督夫人礼佛图》中展现得更加淋漓尽致。
然而,这幅惊世绝伦的壁画,已经不存在了。
它原本静静躺在莫高窟130窟的甬道南壁,被西夏壁画所覆盖。上世纪四十年代,西夏壁画被张大千剥除,使得这幅画受到了严重损毁,已面目全非。
如今我们看到的版本,是已故的敦煌研究院名誉院长段文杰经过长期研究,结合同时代作品的特征手法,竭尽全力“抢救”出来的,成为了敦煌壁画临摹的代表之作。
它其实是一幅供养人画像,而且是唐代同类作品中最大的一幅。供养人即为“出资人”,画作的主角便是其本人,从而可以看作是一幅“肖像画”,足以如实反映当时的人文特征。
画中共有12人,主3仆9。最前面的都督夫人太原王氏一袭红衣,遍布鲜花,钿钗罗帔,一派高贵气质,与后面左顾右盼、窃窃私语的婢女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有人因此调侃道,“她硬生生把礼佛之路走出了红毯的感觉。”
微笑的苦痛:北魏特有的精神状态
我们很容易在北魏的年代目录下,找到佛教艺术的至臻之作。然而,朱红的背后殷透了杀戮的血色,淡然的微笑不过是劳苦大众的精神解脱。
嵇康、陆机、陆云、张华、潘岳、郭璞、谢灵运、刘琨……名仕一批批被送上刑场,万民坑屠更是时有发生,成为不为人知的感慨悲歌。在这样的时代里,佛像嘴角的浅显微笑便是劳苦大众唯一的希冀。
这一时期的作品中,存在着大量描述极度肉体痛苦与超脱的作品。
莫高窟254窟右壁上,有一幅《尸毗王本生图》,讲的是佛祖前身尸毗王为从鹰口中救下鸽子,割自己的肉用来交换的故事。鲜血淋漓的天平准备称量肉体的重量,周遭众人面色或惊恐,或哀伤,只有尸毗王面容祥和,呈现出一种平静之下的诡异美感。
《尸毗王本生图》
就在同一窟中,还有一幅《萨埵太子本生故事》,讲的是前世佛祖自愿跳下山崖,舍身饲虎的故事。壁画毫不避讳血腥之景,甚至为其涂抹上了一层神圣的韵色。正是超越心性的痛苦,造就了超脱苦痛的艺术。石窟无言,只有满目的黑暗与淡漠。
《萨埵太子本生故事》
《九色鹿经变》:一句关于承诺的箴言
《九色鹿本生故事》-调达感恩
这是一个流传甚广的故事,一句关于承诺的箴言。
故事是这样的:恒河边生活着一只美丽的九色鹿,某天救下了一个名叫调达的落水者。调达获救后感激不尽,跪在九色鹿前千恩万谢,表示愿为奴仆,一生伺奉九色鹿。九色鹿说:“我这里水草丰盛无需伺奉,只请你不要将我的行踪告诉别人。”调达指天发誓:“若违背誓言,定遭报应!”
一天夜里,这个国家的王后梦到了美丽的九色鹿。第二天清晨,她向国王说了此事,表示“想用鹿皮做褥子,雪白的鹿角做佛柄”,让他赶快派人捕捉此鹿。于是,国王立即派人到处张贴告示,重金悬赏捉鹿之人,甚至奉上一半国土作为犒赏。
《九色鹿本生故事》-调达告密
那个曾被九色鹿救起的落水者调达看到告示,忍不住重金的诱惑,便带着国王的人马前去捕捉九色鹿。
被团团围困的九色鹿一五一十地向国王讲述了事情的全貌,国王羞愧异常,遂释放了它,并下令任何人不准伤害九色鹿。而那个告密者调达,因违背诺言与背叛救命恩人,全身长满了恶臭的毒疮,遭到众人的嫌恶与唾弃。
《九色鹿本生故事》-带队猎鹿
《九色鹿本生故事》 -揭露真相
《五台山全图》:
“中国第一国宝”的指路牌
1937年以前,中国大地上尚无唐构的影子。甚至有日本学者做出断言:“中国境内已无唐代建筑留存,大唐在日本,不在中国。”梁思成与林徽因对此心有戚戚,决心在苍茫大地上进行寻找,并做好了为此穷尽一生的准备。
梁思成曾在《清凉山志》上读到过五台山区建有两汉时期建筑的记载,也在法国人伯希和的《敦煌石窟图录》中见过大佛光寺的图片。没有史料曾记载过佛光寺被损毁的记录,这些坚定了他找寻到佛光寺的信心。
在佛光寺拍摄的彩塑。
佛光寺东大殿。
被誉为“中国第一国宝”的佛光寺,正是以这样的奇缘与敦煌交织在一起。莫高窟61窟中这幅传奇的壁画,也因此被赋予了不一样的意义。
走进美术馆的大门,便能看到这幅悬挂在一楼大厅中的巨幅壁画。这也是敦煌莫高窟最大的一幅壁画,是古代先人印刻在石头上的“全息地图”。
图中既有飘然入圣的佛与诸菩萨,也有人间百态与市井烟火,还包含200多座建筑、500余位人物,可谓“一壁看尽八百里山川”。
飞天莲花:平棋藻井的美学巅峰
再看看那些精美异常的平棋与藻井,它们用单纯的艺术布局隐藏了足够领先的美学密码。恍然发觉,原来一千多年前,我们也曾站在艺术的巅峰。
佛像之外、窟壁边缘的敦煌,那些用作点缀的平棋藻井图案同样足够震撼:
莫高窟407窟,可爱的“三兔共耳”蕴藏玄义;
“三兔共耳”平棋
莫高窟257窟,游泳的天人在宝池里自由嬉戏;
莫高窟257窟——游泳天人
莫高窟329窟,飞天在莲花与彩云间追逐游弋;
莫高窟329窟平棋——“莲花飞天”平棋
等一下,为什么这里的飞天是黑色的?
关于这个问题,专家此前曾有过争论。有人认为这是由于古代敦煌作为丝路的节点,带入了一些西域的成分,而黑色飞天就是黑色人种的神仙,是文化融合的见证;也有人推测是由于这些窟龛位置较为靠后,工匠的颜料已近告罄,无奈只能用黑色颜料来“掩人耳目”。
长期的争论不休后,专家们最终决定取下一点样本进行化验。黑色飞天的神秘面纱由此终被揭开:原来那些“黑颜料”原本都是红色的朱砂,在长时间的氧化后由鲜红色变为了黑色。千年弹指间,敦煌与我们开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玩笑!
水月观音:世间优雅的集合体
一撮蛇形髭,一绺细短髯,两只飞燕目,璎珞多宝冠,这一黄一黑两尊水月观音绘制在榆林窟第2窟的西壁门两侧,散发着金碧幽雅的魅力,是西夏壁画中的上乘之作,被称为“敦煌最美水月观音”。
石青、石绿等清冷色调,配合流云、山月与灵鸟,勾勒出“青莲翠竹月,山岫出云端”的世外尘嚣。画面以外,龙女正双手合十躬身礼拜,善财童子翩跹然踏云而来。
更有趣的是,画面右下角的角落里,正是“唐僧师傅西天取经”的故事。
大唐的玄奘和尚一路西行,也被定格在了沿途的史书卷帙与石刻书画中。他曾在瓜州停留数月,与当地人民结下了不解之缘,于是这位神话般的高僧,终究成了神话的一部分。
直到此时,孙悟空还只是玄奘的一位胡僧“向导”。由于吴承恩还未登场,这场西行求法的漫漫长路还没有与年代更早的八戒、沙僧取得联系。
当然,骑马取经的形象,很容易让人联想到敦煌另一幅著名壁画:《化城喻品》。
《化城喻品》:
比“西游记前身”更早的冒险故事
化城喻品,是佛典《法华经》中的重要譬喻。“化城”,为一群人取宝途中的暂时休憩之处。
此场景广泛见于各种版本的《法华经变》中,其中最精美的莫过于莫高窟217窟这幅。
这个故事,讲的是一群人去远方找寻宝藏,历经千难万险后已疲惫不堪,驻足观望,心生退意。这时,人群中最有智慧的“导师”为大家幻化出一座亭台楼榭的城池,众人欢欣异常,沉溺安逸,不愿继续前行。
导师见状,又将城池化去,并由此点拨众人不能满足于暂时的安逸而放弃了长久的目标。众人于是皆追随导师而去,最终找到了宝藏。
普遍认为,《法华经》创攥于秦汉时期的古印度、尼泊尔等地,晋时传译入中国,比《西游记》的前身《大唐西域记》早了两三个世纪。
《西方净土变》:敦煌“宏大的代名词”
榆林窟第3窟《阿閦净土变》
《西方净土变》是敦煌壁画中最重要的一类题材,根据所依据的典籍又可分为《阿弥陀经变》、《无量寿经变》和《观无量寿经变》三种。
它表现的是阿弥陀佛西方极乐世界的功德庄严,因而往往描绘极其宏大的场面。
这类画作的代表作众多,如莫高窟220窟的《无量寿经变》,莫高窟172窟的《观无量寿经变》,莫高窟217窟的《观无量寿经变》,榆林窟第3窟中的《阿閦净土变》等。
莫高窟172窟《观无量寿经变》
它们无一例外是佛国净土的典型代表,挥洒着宏大的世界观与建筑山水的巨大想象力。
多以“透视画法”在平面上塑造出层次,建筑以横纵两向延伸出递进的深度,穿插以诸佛与菩萨、莲台宝池、神兽乐器等,令人眼花缭乱。
即将出门的时候,我偶然瞥见一件破损的佛像,上部的缺失丝毫不影响我在大脑中重塑它原本的样貌,窥见它曾经的婀娜与深情。
佛像如此,敦煌亦如此。或许文化是个脆弱与坚韧的集合体,我们为失去而扼腕,又为失去而加倍珍惜。
敦煌已经成为一个符号,一段漫长时间与绵长历史的代名词。或许我们永远无法确知它的全貌,也无法破解它的每一个秘密。
文化就像深渊,它的留存与揭露,都是一层层铺陈而成的产物。而我们所见证的,究竟是故事的开头,还是结尾,亦或是故事本身呢?
以文字温暖心灵,以色彩阅读世界。
《龙门石窟|我看到坠落1500年的繁星亮起》
《敦煌,千年悠长》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途鸦er”(ID:tuya_er)。大作社经授权转载,该文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大作社平台仅提供信息存储空间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