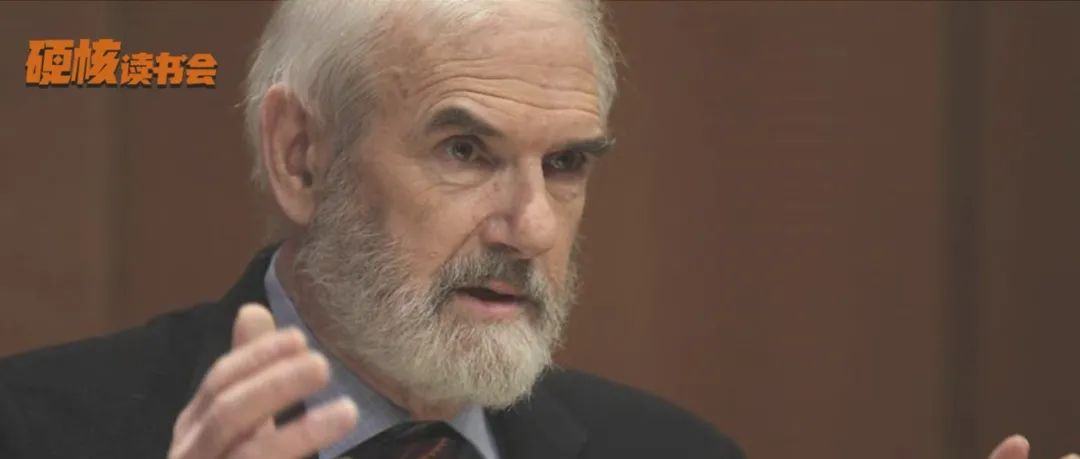✎作者 | 桃子酱
✎编辑 | 程迟
“秘密花园”
“我们在西黑文住,有一块3英亩的花园,种了许多花。每次当我说,我们再开垦一个bed吧,史先生就会很累。常常有小鹿来偷吃玫瑰,我就会训斥它们。史先生已经退休,主要是看书、写作。答应别人的要写完,交出去也不大关心销量。我们都喜欢读诗、小说,常常分享好的段落。我们也爱看电影——1935年以前的美国电影,五六十年代的英国电影、意大利电影;法国新浪潮是年轻时喜爱的,如今不敢回头再看,因为,它们好做作啊……”
这段记述来自记者李宗陶的《史景迁的历史之味》一文,讲述者是史景迁的夫人金安平。2014年,史景迁夫妇访问中国。从北京、成都、西安到上海,时年78岁、神似肖恩·康纳利的史景迁所到之处,都得到了学术明星般的待遇,李宗陶正是随行记者之一。
当时有媒体记录了这样的细节:在北大的学术讲座上,有听众在提问纸条上直接表示对史景迁的景仰:“看见你就像看见摇滚明星。”史景迁困惑于自己在中国受到的明星级待遇,于是问翻译:“我一个外国人,用英文写作和演讲,为什么中国人对我这么感兴趣?”他的翻译回了一个字:“帅!”
史景迁为书迷签名/视觉中国
史景迁的第一次中国之行是在1974年,他和十几名耶鲁大学教授来中国转了一圈。其中一位数学教授备受礼遇,因为“那时的中国人热爱数学”,而史景迁“什么粉丝都没有”。上世纪80年代末,他再度访华时,在北大,“被禁止随意出入”,仍然没有什么人认识他。2000年前后,他的作品开始被译介到中国,由此,他收获了一大批忠实读者,人们希望从这个外来人这里得到关于中国历史的别样解读。
在接受《人物》杂志采访时,史景迁在耶鲁的第一个弟子、原香港城市大学文化中心主任郑培凯也讲述了史景迁这个“很英国的英国人”对园子的喜爱,说他从春天起就戴一个草帽,像农夫一样,到园子里剪树莳花;他的园子下面、一条小河旁,本来是一片沼泽地,被他改造成他所称的“秘密花园”。
郑培凯本打算2019年暮春时节约史景迁到江南走一圈,去逛西湖,去张岱的故乡,因为那是史景迁心目中“文化的中国”,也是他最开始研究的中国——史景迁的第一部著作,正是基于他的博士论文的《曹寅与康熙》。“我推想,他最想的大概就是像康熙、乾隆一样能够下江南。”郑培凯表示。
《曹寅与康熙》
[美国] 史景迁 著,温洽溢 译
理想国 |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3
但史景迁没能成行。起飞前他突然晕倒,这是早期帕金森病的症状。两年后,他因帕金森并发症去世。这当然是个遗憾,但郑培凯也表示,史景迁“其实一直生活在中国的整个历史文化的情境里面,一个很美好的精神空间,也算是幸福了”。
一位历史学家的“前朝梦忆”
郑培凯最喜欢《前朝梦忆》,他猜想史景迁本人最喜欢的也应该是这一本。然而,正是这部《前朝梦忆》对张岱作品的大量引用、以及对文献的一些曲解,让读者对它的评价截然不同。
作家张向荣读到的第一本史景迁著作,就是《前朝梦忆》。他的第一感觉是“乏味”:“凡是读过张岱原著的人,读《前朝梦忆》只会产生读中文系毕业生拼贴畅销书的感觉。全书有一半以上都在引用张岱的原著,只不过史景迁用自己的角度拼贴了一下。于是,这些原文既失去了小品文的风致,也并没有清晰地呈现出作者的意图。”
《前朝梦忆:张岱的浮华与苍凉》
[美国] 史景迁 著,温洽溢 译
理想国 |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9
近代史学者汪荣祖写有《梦忆里的梦呓》一文,一一指出《前朝梦忆》中史景迁对张岱原文的曲解之处:如全书第一段,即“张岱居处前有广场,入夜月出,灯笼亮起,令他深觉住在此处真‘无虚日’,‘便寓、便交际、便淫冶’”(温洽溢译)这一段,即有两三处谬误——“士女凭栏轰笑,声光凌乱,耳目不能自主”中的“士女”,史景迁理解为“年轻男女”(young men and women),其实士女就是女士,无关男士;而士女们到夜深“星星自散”,史景迁则解为“星星们散去了”(the stars disperse),把形容词当成了名词。
汪荣祖更进一步在《史景迁论》中提出了一个尖锐的疑问:史景迁到底是在写历史还是在写小说?
史景迁确实以会“讲故事”著称,他的一些作品,读来不啻精彩的小说。张向荣就很欣赏史景迁的《利玛窦的记忆宫殿》,他认为这部作品具备现代主义文学的气质和结构。也有人不认同史景迁的文学化手法,他们通常会引用钱锺书对史景迁的那句揶揄——“失败的小说家”。
《利玛窦的记忆宫殿》
[美国] 史景迁 著,章可 译
理想国 |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10
即使用小说家的标准来看,史景迁也是叙事大师。在张向荣看来,史景迁的著述为历史写作者提供了范例:他的每部著作采用不同的叙述方式和结构,让后学者感受到历史学者的想象力可以达到什么程度、他们又是如何突破历史与文学的边界的。
历史学者到底需不需要想象力?对此,历史学者王笛在接受《南方都市报》采访时持肯定态度。但王笛也指出,历史写作的想象有一个前提,即你的论述是基于历史记载还是自己的推论和想象,一定要告诉读者。王笛说史景迁就做到了这一点,在《王氏之死》中,他引用《聊斋志异》的片段去描述王氏的梦境,并告知读者这段文字的来源。通过这些文学性的叙述,史景迁渲染的是一种“在场感”,让读者回到历史情境中。
《王氏之死》
[美国] 史景迁 著,李孝恺 译
理想国 |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9
历史写作的“在场感”
《太平天国》
[美国] 史景迁 著,朱庆葆 等译
理想国 |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9
《哈德良回忆录》
[法] 玛格丽特·尤瑟纳尔 著,陈筱卿 译
上海三联书店,2011-3
文学和历史的结合
“对这对夫妻,我们知道的是:在1671年年初,他们已经结婚,住在郯城西南八英里归昌集外的一个小村庄。他们很穷,任某靠着在别人的耕地上做佣工维生。他们的家只有一个房间,里面有饭锅、一盏灯、一床编织的睡席和一个稻草床垫。我们也知道结婚后有六个月,王氏和她的先生及七十岁的公公同住,不过这个老人最后搬到一英里外的另一间房子,因为他跟她处得很不好。此外,我们知道王氏白天大部分时间都一人孤单在家;知道她缠了脚;知道她没有小孩,虽然隔邻有个叫她婶婶的小女孩;知道她的家面向一片小树林;并且知道在某个时间,因为某个原因,随着1671年的流逝,她跑掉了。”(李孝恺译)
《王氏之死》的这个开篇,以今天的标准来看,堪称非虚构写作的范本。当然,因为它以历史作为题材,所以应该称为“历史非虚构写作”。
历史非虚构写作是近年来兴起的一个概念。关于历史非虚构作品和历史学术著作的区别,按照张向荣的理解,有两个层次:其一,是否采用学术标准。在历史非虚构作品中,文学可以作为方法论使用。其二,是否表达作者观点和情绪。写作者在历史非虚构作品中表达的观点,可能在学术界看来没有那么重要,甚至是一些常识,但基于向公众传播的目的,写作者仍然会采用。
此前,史景迁与历史学者卢汉超对谈时,也谈到了“literature”和“fiction”的区别。史景迁认为,当我们使用“literature”一词时——无论是指“文”或“文学”,我们是用它来传达一种品质、一种评判,或者是如何遣词造句;当我们用“fiction”一词时,意指一种方法,而这种方法除了广义上的合情合理外不必以事实为依据。将历史与文学结合和将历史与小说结合,不是一回事。
在史景迁看来,文学是一种哲学传统,“所以,如果说我把文学和历史相结合,这只是意味着我对史学的写作风格有着激情......我试图把一本书建立在这样的架构上,使其既在一个层次上准确,又在另一个层次上表达感情,并给所述故事以更丰富的背景。这就像运用艺术一样,使历史写作接近艺术以取得更深层的效果。”
从这个意义上说,史景迁可以说是通过自己的写作,示范了历史非虚构写作的种种可能。比如《王氏之死》,像王氏这样在史料中只占据区区几行字的小人物,如何让她显得真实可信?史景迁的做法是:通过同时期、同地域的《聊斋志异》的文本,为这个人物赋予情绪。
早在2005年,媒体人庄秋水就撰文提出,史景迁的著作,是西方典型的非虚构写作——“它用一种更具想象力的方法,对历史进行侦查,它允许作者把自己融入到时间当中;也允许作者从一种旁观者的角度去看待所叙述的人物和事件”。
史景迁(右) 曾获得莱昂内尔·盖尔伯文学奖/视觉中国
史景迁向卢汉超表示,自己和“师祖”费正清的不同之处在于,费正清的目的在于辅助美国的政策(比如他那本《美国与中国》),“而我写作的目标是鼓励人们了解中国”。“即便我的书看上去有些像人们所说的大众读物,但我总是为读者提供了专业的和更深入的阅读书目,告诉他们下一步怎么走,希望他们能够发展出自己的兴趣。”
“四十年后,人们仍在阅读我的书,这不是因为我的写作方式很时兴,而是因为我触碰了这些故事的本质。”2014年,史景迁如此表示。
· END ·
作者丨桃子酱
编辑丨程迟
校对 | 向阳
喜欢这篇文章,请让我们知道 ↓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惊蛰青年”(ID:wakinglism)。大作社经授权转载,该文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大作社平台仅提供信息存储空间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