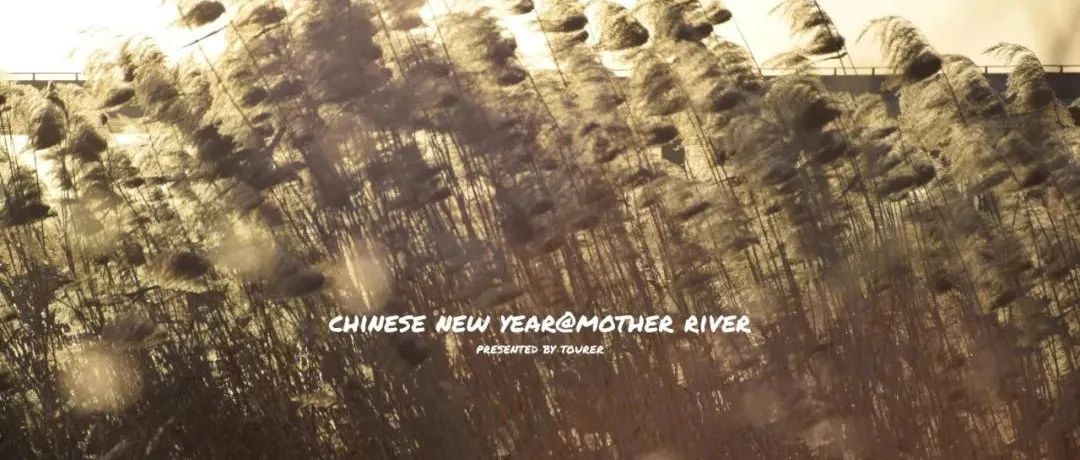途鸦er,分享旅行之美
每次过年,年味渐浓的时候,总会归乡思源,想起小时候的事来。
想起一家人骑车去很远的太公湖摸鱼捞虾,想起攀在母亲自行车后座上瑟缩着挪向幼儿园,想起在冰天雪地包裹的围炉里包饺子...
也会想到淄河。
临淄人,长到几岁也会记得淄河这个名字。
当我在某一年的问答现场被要求列举出中国最著名的几条河流,我的脑海中便冒出这么几个名字:
长江,黄河,淄河...
.
太公湖上的水鸭。
淄河滩,太公湖,一个意思。
记得小时候,傍晚时分爸妈下班,会牵着我或是骑自行车载我,去东泰商城或者利群超市买东西。
那是一个孩子最幸福的时光,琳琅满目叫不上名字的糖、薯条、话梅、蛋卷看的心焦。
但最重要的,是在那一个小时里,可以堂而皇之地不写作业。
周末,我们会走得远一些,做好长途跋涉的准备去到更远的东泰广场或利群商厦去逛街。
其实那时分不清它们,直到后来才明白东泰广场其实就是东泰超市的“母亲”,而利群商厦与利群超市也是直系亲属关系。
若是逢年过节或是周末郊游,妈妈就会骑上单车,花费很久很久的时间带我去太公湖捞鱼摸虾。
那时候的太公湖,波漾水清,鱼虾成群。
一网子下去,再抻起来时便平添了十分重量,自知是那蹦跳的虾子之功,不免内心窃喜。
未见收获而先自喜乐,这恐怕是童年的特权。
不过,边际效用递减的自然论断,也适用于五六岁的孩子。
当桶里的虾子足够多了,新捕上来的透明小家伙也不再引起我过多的乐趣。
于是回家来炸了一盘,摊在桌上,大大的,占了一半的面积。
他们却并不十分衷情,只偶尔夹取,于是尽数都给我吃了。
如今早已忘了味道,但那从家到湖边,再从湖边到餐桌上的距离与野趣,一直贯穿着十几二十几年的回忆。
这段距离,便是对一个生于临淄、长于临淄的孩子来说,最远的距离了。
就像大海之于海滨之城,外面就是浩淼无尽的,广阔的世界,而彼时的我们都看不到彼岸。
大多数时候,看不见的才最美,就像幼年时看不见湖那边的广阔世界,成年后却望不尽孩童时的那份天真无忧,直叫人想端起望远镜,面向自己的过去,看个明白。
直到若干年后某个春节回乡,满鬓染霜的妈妈提起再去太公湖转转。
当我打开地图发现那需要“长途跋涉”才可到达的商厦,不过1.2公里,而那“远在世界尽头”的太公湖,也只有区区4公里的时候,我简直不敢相信我的眼睛。
对于在大城市里奔波惯了的我,那不过是一站地和三站地、骑不骑共享单车都吃不上一顿准点晚饭的距离。
可见临淄确实是座小城。
太小了。
小到保存不下两三千年历史的遗存。
作为齐国故都,齐文化的故地,遗憾是始终绕不开的。
古老的齐国,除了三两器物,几尊佛像,坑坑洼洼的城墙排水口和一些亦真亦假的所谓遗址外,几乎什么也没有剩下。
两千多年里,那些城墙不知曾伫立多久,但总归是慢慢消失在横七竖八歪歪斜斜的风里,成为人们口中跟在曾经后面的谈资,与历史书上黑白线条勾勒出的假想图。
临淄齐文化博物馆中的齐国故城模型。
临淄有个天齐渊,但并不有水源,后来才发现竟是个山寨货。
我也曾顺着网上稀稀疏疏的描述,试图找寻那真正的天齐渊,却总迷失在横七竖八的小巷子与沙尘漫天的高速路边。
后来那种冲动随着一次次的失望慢慢淡下去了,直到完全释怀。
我果然不是个特别执着的人,亦或是这并不十分出众的地界不太值得我一次次的为之趋之若鹜。
于是又回到那个假的天齐渊公园,流连于一座座并不太高大的山头。
背着巨大的相机走上天齐渊公园,不免显得有些格格不入。
不仅仅是因为临淄并非是个旅游城市,也绝少有人玩摄影。
更重要的是,临淄人对自己家乡的印象,大多还停留在十年以前的“黄天厚土”之上。
这样清的蓝天、这样大的公园,是什么时候冒出来的呢?不太有人说得清楚。
天齐渊公园。
天齐渊公园对面,是已废弃多年的胶济铁路。
那是一个时代的代名词,是那个工业化临淄的缩影。
小时候,总不敢在它旁边稍作停留,担心会有不长眼的火车呼啸而来,造成不必要的压迫与麻烦。
但终于有一天,有人告诉我那条铁路早已废弃多时了,那是上世纪30年代梁思成与林徽因乘坐的铁路,黑黝黝的身体留下了那个时代特有的回忆。
我也不便多问,只觉遗憾自己竟莫名其妙地担忧惧怕了这么久。
有一天,我终于得一空闲,爬上了那条铁路架在高处的轨道。
冰凉的铁轨与枕木交错着,一条条规则地错落,像是堆积起来的、数不清的时间,我看向一边,是层层叠叠的大楼与街道。
另一边,是一望无际的远方,隐没在模糊的天际线里,谁也不知道那边有什么。
铁轨的另一端,与太公湖的另一端,是同样的世界吗?
小时候的我没有答案,现在的我不去思索答案。
人怎么能拗得过铁轨呢!我想着,哑然失笑。
老胶济铁路。
小时候与母亲谈起这些,总少不了谈及她无法治愈的鼻炎与我的结膜炎:那都是四面环厂的临淄生活最为无奈的“馈赠”。
那时候的临淄,天总蒙着一层灰,空气里充满着摄影师口中的“质感”与“颗粒”。
读书的间隙,母亲总对我说,走出去吧!逃离家乡,去更广阔的世界,那里能看得见星河。
很多年以后,当我乘着北上的火车,沿着淄河岸缓缓靠近家乡,与那条早已废弃的铁路并肩而行却互不交叉,我总会想起两个模糊不清的背影。
当年的林徽因与梁思成,也是这样从一座城市奔向另一座城市,一个起点奔向另一个起点。
那时候的他们,是怎样的姿态呢?是倚靠在窗边吗,还是躺在卧铺上呼呼睡着大觉?
我记得林徽因在散文《窗外》中,或许曾描述过这份灵感的来源,想来应当是依靠着的。
她看到了什么呢?
总之在他们的手中,六和塔的疾病有了药剂,赵州桥避免了坍颓的命运,正定文庙第一次在时间之海里有了来处。
他们拿着放大镜,看透大半个中国的沧桑古今。
在他们奔跑的背影里,这条漆黑的铁家伙一路从山的那头延伸出去,向西北横冲直撞。
破旧的,就该逃离么?我在那些挣扎的岁月里问自己。
没想到,我在厦门吃椰子的那几年,家乡一直在种树、关厂。
这几年,每每回到家,见到久违的蓝天、白云,心里总觉不太真切。
虽然太公湖已不再有捞不完的虾子,或许它们都被我捞上来吃了吧?
听人说,天齐渊还要扩建,未来将沿着太公湖引的水一路修成河滨公园。
那该是怎样一幅图景呢?
我不知道,但总觉得内心充满期待,不由得又端起相机,对准了新修的木栈道。
木栈道温暖的阳光里,无数个背影在奔跑。
临淄日落。
当我写到这里的一刻,外面正下着雪。
上一次去太公湖的时候,湖面正结着厚厚的冰,嵌满了气泡和枯枝的冰面一路歪歪扭扭,延伸到湖中心依然奔流的水流边缘。
散步的大爷,牵着小孙子,三三两两地在湖堤上走着。
地图缓缓铺开,太公湖其实是淄河上一段开阔的河面,但幼时坐在妈妈后座上的我,以为那片“湖”有尽头,以为父母永远不会老,岁月永远停留在童年并充满光彩。
波光粼粼的水面无从何来,也不知何去。
后来当我明白了太公湖不过是奔腾千里的淄河上的一小段,我开始意识到,所有的事情都有过往与来处,而那些看似精彩的湖泊,不过是一段漫长旅程中的稍事停留。
我还是习惯称它为“太公湖”,习惯走得很近,去注视映在冰面上的我的脸,从幼年,到少年,再到青年。
那个孩子拿着网兜,挪动着笨拙的身体,试图在日夜不停的淄河里兜住些什么。
以文字温暖心灵,以色彩阅读世界。
《西子湖|一汪水,一汪岁月》
《石塘 | 一个小鱿鱼引发的裸辞》
感谢你的阅读、转发和在看。
下面是1个抽奖链接按钮,2月9日晚上18点开奖,一共188元,18个红包,感谢大家的支持。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途鸦er”(ID:tuya_er)。大作社经授权转载,该文观点仅代表作者本人,大作社平台仅提供信息存储空间服务。